|
|
|
|
|
天意指引
在卓玉倚着床畔等待着孩子降临的那些日子,达旺也辗转反侧地难以入睡,不过让他如此心积虑的却另外一桩完全不同的事情。 十多天以前,一个身着藏袍的中年人,出现在了达旺的帐篷内,待他脱去狐帽,取下假须之后,达旺便高兴地引了上去,“李副师长。真没想到还能见以你。” “我也没想到,真是上天保佑啊!” 来人李迅予是原国民党驻重庆249师副师长,曾在黑水任县长,与达旺多有交情,在刘邓大军以推枯拉朽之势胜利攻克重庆之后,李迅予就一直去向不明,或死或逃或隐,猜测颇多,今天突然出现。达旺料想必有大事发生。 果不出所料,深知达旺脾性的李迅予开门见山,“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跟兄弟连手合作,建立黑水根据地,共同对付共产党。” 达旺默不作答。 黑水地处大雪山深处,地广人稀,交通闭塞,部队给养运输困难,加上当地为人少数民族聚居地,不便筹粮,又因为黑水是和平解放的,解放军为了表示一个信字,并没有在黑水驻扎多少部队,除了三个连之外,其治安基本由县基干大队负责,这是国民党的原黑水保警队,有200多人,十挺机枪,其队长便为上文李迅予提到的王中,而县人民政府一时也还没来得建立基层政权。因此鉴于上述种种“优势”,替伏已久的李迅予终于跳了出来,一方面到处煽动鼓诱,一方面积极向台湾谎报军情,他大言不惭地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反共的大旗已拥兵五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这些失实的报告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为了配合朝鲜战场与志愿军对峙,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中共的后方埋一颗定时炸弹,以达牵制作用。现在,这颗“定时炸弹”已经有了,他们决定使它的威力扩大十倍,甚至百倍。 而对台北来讲,黑水的战略价值也极大,它处于川、藏、甘、青四省边区,因此,黑水基地能策动四省的武装发展。若缅甸的李弥将军向云南发展,便可使甘青云贵川藏六省连成一片,大陆的胸脏地区就会乱起来,那么共产党的江山也就坐不稳了。因此,当美国主动提出愿派飞机空投时,台北不亦乐乎地接受了。 李迅予获悉亢奋三尺,竟连夜乔装来找达旺。 “兄弟,我信任你,不论你干,还是不干,我们都是兄弟,”李迅予又加了一句,“二十天后,我来听消息。” 1952年4月8日清晨,伴随一阵阵花般的太阳雨,一个漂亮聪慧的女孩降临在了美丽的山寨。 一个月以后,即1952年5月15日清晨,山寨年轻美丽的女土司坐上了松岗部落迎新队牵来的白马上,从此,卓玉开始了嫁为人妇的日子。 整个婚礼隆重铺张,狂欢了七天七夜,这对一直过着单调的几乎一成不变的游牧生活的牧民来说,真可称得上是一个重大的节日。方园百里,闹了个轰轰烈烈,但人们却绝少看见新郎新娘,偶尔有外来的人问起,人们便会很自然地甩手指向遥遥的桑林湖畔,诡秘而暖昧地添上一句“新帐”,然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举杯一饮而下。 可是事实上,那立在美丽的桑林湖畔的新帐内,除了心事重重的卓玉和几个仆人之外,根本没有新郎的影子,新郎正在另一处忙得不可开交。 就在卓玉坐上白马的同一时刻,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从台北桃园机场缓缓起飞,向海南方飞行。机舱内的一名中年男子忍不住掀开窗帘最后看了一眼逐渐变小的台湾,一行泪潸然而下。坐在他身旁的同伴轻轻说:“但愿是再见,而不是永别。” 飞机进入海南岛上空后,开始朝大陆飞行,飞行员是二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曾参加过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对中国大陆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为了躲避东海岸的雷达侦察,飞行高度一直在1万米以上。 下午5点,飞机到达成都上空,然后向西飞行,顺着岷江直奔黑水,晚8点,抵达黑水吉日上空。李迅予等人在吉日地面,准备好了空投场地:两块白布拼成一个规则的“T”字,旁边燃几堆烟火,飞机在吉日上空转了一圈,看清目标。首先空投物资、武器、电台,然后特派专员跳伞。 一切颇为顺利,所有的人们都轻轻松了口气。 “我是李迅予,欢迎你们。”李迅予迎了上去,一副兴高彩烈的样子。 这次空投物资有:黄金150两、电台5部、卡宾枪80枝、手枪50支、机枪8挺,MTM炸药30公斤、密码本30套、伪造人民币10亿元、文件3包、传单2捆。 空投的成功使李迅予得意万分,决定迅速叛乱,具体日期定在1952年6月15日。然而正当他们举杯庆祝之时,那位王牌飞行员却因为飞机突然的故障,而葬生在蜿蜓的秦岭之中。 达旺无法说清那天自己的感觉,他只知道在那一刻,他可以为这个女人抛弃整个世界。然而令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却是:就在那天晚上,他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本来可以带给自己无限幸福的女人,而和几个不太喜欢的男人一起站在狂风飕飕的山脚下,去等二个什么也不是的空降专员。 一跃下马,达旺冲进了帐内,卓玉和梅吉同时转过头来。 “即然哥哥回来了,我也就该回去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梅吉起身告辞,她眼睛中一脉饱含的深意让达旺和卓玉同时有了一种莫名的哀感。 屋里一下子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彼此的喘息声,在这本来就只属于他们两人的新帐内,达旺和卓玉却有些手足无措。 他想走近她,她却想后退。 可是他无法控制住自己有兴奋,无法在透视出她衣裙底下那丰盈、成熟的女性曲线之后,还道貌岸然地维持自己的尊严,此刻他的灵魂已暴露无遗。 想要卓玉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令达旺的肉体深觉痛苦。 于是,他猛然地扑向了她,将她推在地毯上,他的身体压在她的身上,那双大手去扯她的裙子,而渴望已久的唇也在急切地寻找着……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卓玉开始歇斯底里般大叫,挣扎着用膝盖去踢他的鼠蹊部,伸出手去抓他的脸,还用牙齿去咬他的胳膊……她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地喊叫。 他捉住她的手,保护自己不被她尖锐的指甲和牙齿弄伤。此刻,躺在底下在卓玉,就象一只凶狠的野狗。 她的疯狂让他大吃一惊,然而最让他惊奇的是:她骂他流氓、骂他强奸犯、骂他无耻、下流,而在几天以前,她曾经那样平静地和他举行了婚礼,接受了祝福的哈达。 她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吗?或者是她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丈夫,这个令人沮丧的念头使他放弃了一切想法,他从她的身上下来,转身向帐外走去,门口,二个年幼的仆人正好奇而惊恐地望着他。 “给我滚回去,”他大声地喝诉,“你们全都给我滚回部落去,一个也不许留下来。” 仆人们都小心翼翼地溜了回去,达旺独坐湖边,咒骂自己的愚蠢,而此时,浪漫的玫瑰色的晚霞正挣荣缤纷。 转眼之间,一切都过去了,只有岭峻的现实一动不动。 在达旺年轻的时候,他遇到过很多女人,他和她们周旋做乐、逢场做戏、寻找刺激。可是他却从没有在乎过她们,没有把她们放在心上,更不曾尊敬过她们,那时候,女人在他的心里和一堆粪土等价。 后来,确切地说,在他三十五岁那年,他遇见了沃日土司的女儿朗萨。她的美丽、典雅和神秘触动了他的心弦,他被弄得神魂颠倒,变得与年龄不相符的傻气和多情,他渴望她的爱抚,渴望她的柔情,渴望她身上所有的一切。那时候,他所能对自己说的唯一一句话便是:天哪,她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可是,朗萨却躲着他,用冷酷无情的眼睛嘲笑他,义无反顾地拒绝他。她对他所有值得炫耀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的地位、财富、英勇、高大……这所有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微不足道,一钱不值;都如粪土一般,那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对女人有过怎样的苛刻和偏颇。 可是,他却依旧无法隐藏心中冲动的激情。 于是,那个可怕的午后来了。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怎样一个午后:万里草原,天地寂静,细风吹拂。天生丽质的朗萨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而那一刻,他也正如痴如狂地在想她。 多么巧合,简直就是上天的安排。 他“呼”地站起来,急匆匆地奔向她,粗暴地撕开她的衣服,那一刻,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得到他,无论什么代价。 可是,她的安安静静却轻而易举地怔住了他。 于是,他把头深深地埋在她的胸里,去躲避那双令人心寒的眼睛,可却没能躲过那注定将终生缠绕他的声音,那声音曾经那样平静而充满恐怖地从她嘴里传出:“如果你不介意一个被亲生父亲糟蹋过的女人的话,那么就随你的便吧!” 那声音——那从肺腑发出的声音——一字一字地深深震撼着他的心。 一瞬间,失落、羞辱、悲哀全部罩在了他的身上,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 于是,达旺用一把藏刀结束了朗萨的生命,他认为只有死亡才能使她继续保持自傲和清高,而残忍一点的死去会让她觉得平衡和解脱。 几个月后,达旺就用这把藏刀切下了沃口土司那苍老污秽的头,他烧光了土司美丽的庄园,也烧去了心中最美丽最疼痛的爱情。 女人是粪土的想法再一次占领了他的思想,但这一次,他不得不承认,有些女人之所以成为粪土,是因为她们碰上了象粪土一样的男人。 二年后,达旺娶回了一个妻子,一个非常谦逊单纯的女人。可达旺并不爱她,他之所以娶她,只是因为他想要一个来路明确的孩子,所以,当她被证明实在无法生育之后,达旺就果断地抛弃了她。他要你,或不要你,都那么坦然。 他记得那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冬日,被抛弃的妻子收拾好行装,准备带达旺给她的牛羊回到草原深处的娘家,这时候,达旺唯一的弟弟来到帐内,他直接了当地说:“哥哥,如果你不要这个女人,那么我来要她。” “你疯了,她不会生孩子。” 鉴于自己也有过一次堕入情网的经历,达旺知道弟弟是真正倾心于这个女人了,不认怎么样,这个女人比那些街头上一天到晚只知道卖弄风骚的女人要强得多,那么,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弟弟和曾经的妻子去了草原深处。两年后,有人带出话来,说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生活是艰苦些,不过挺平静,挺温暖。 而他,生活得很富贵,却即不平静也不温暖,更不要奢望有什么可爱的孩子,真是应了一句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俗话: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不是的,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的却是必须要面对的。 此时,达旺心中突然对去年的赛马会有了极至的愤恨,是的,如果没有那场可恶的赛马会,他就不会遇见卓玉,不会被她的美貌和灵气所打动,不会像一个傻呵呵的年轻人那样去求婚……当然,也不会在举行了婚礼之后,才发现她原来厌恶自己到这般地步……突然,一声尖叫从帐内传来,达旺嗖地起身,飞奔了过去。
在昏黄的月光下,他看见一条巨大的灰色身影扑向卓玉,便本能地抓起手松措准射击,中弹的大野狼痛苦哀号,转身冲向达旺,几乎转眼之间,野狼尖锐的牙齿便撕裂了他的衣服,同时,一股火辣辣的疼痛直往心上冒。 还好,枪还在手上。 卓玉扶着达旺上了马,随即,她也一跃而上,双手拦腰抱住达旺,抓住他胸前的僵绳,一声吆喝,马便放开速度跑了起来。 回到部落,达旺立即召来手下,安排人员去保护牲畜 达旺躺在帐内,缓缓睁开眼,敞开胸膛深深呼吸,直到头脑清醒一些为止,却突然发现卓玉坐在床沿,显然已经坐久。 “还行吗?”卓玉扶达旺坐了起来。 仅仅为卓玉这句话,达旺也愿意让狼再咬上几口。 整整五天,卓玉都跟随在达旺的身边,照顾他,替他做所有需要用手做的一切,这时候的卓玉与那天桑林湖畔新帐内的卓玉判如两人。那种善解人意,轻柔的本性,她直到现在才表露出来。 “你的伤口很快就会好。”那天晚上,卓玉一边往伤口抹药液,一边对达旺说。 他伸出手轻轻地把她拉向自己的怀里,轻轻地爱抚她,用胡子蹭她光洁的额头,让渴盼的唇在她的脸上、脖颈上,胸前留恋忘返……一个好女人是男人的天堂。 在她的生活中,林浩基的这一页已经彻底地翻了过去。 林浩基和另外二个身军装的人走了进来。 话正说到这时,卓玉掀帘而进。坐在垫上的林浩基不由一怔,卓玉也有些慌乱。 卓玉的那双眼睛即美丽又温情,让达旺好生感动,当然,他绝对不会知道卓玉这所以这么做全是为了给林浩基看看。 “我的伤口已经没事了。”他从心底里感谢妻子的温情。 此时的卓玉心中百感交激。面对着这个她曾经最爱,并且现在也爱着的男人,她的心好生痛疼。她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命运捉弄,他们三个将会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他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快乐,怎样地美满,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家散人离,可同时,她的悲伤也加重了她对他的怨恨,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他,她怎能不恨他?怎能不对这个道貌岸然地坐在这里的家伙耿耿于怀? 而此时的林浩基也正因为他们彼此眼波中流露出的爱意,正妒嫉得心中阵阵作痛,这痛当然不免也生出怨恨来:才六个月,你就嫁人了,可见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在我痛苦的时候,你正身着新装做你娇滴滴的新娘,用你吻过我的双唇去吻他的眼睛,当然,他也会紧紧抱住你,就像我曾经抱过你那样……他不愿再往下想了。又何必自己给自己制造痛苦?他真后悔今天没有去任何一个别的部落,而跑到这里来看如刀子般割上心的亲呢。事实,今天早上他之所以在那么多部落里选择了松岗,唯一的原因便是他想看一眼卓玉,如今看到了,心却更加无法平静。 爱恨同源,啊! 突然,七、八个手提枪械的壮汉冲了进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下了林浩基和同伴的枪,用牛皮绳将他们捆绑起来,拉出帐外。卓玉目瞪口呆,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待她回过神之后,帐内已经只剩她一个人了。 原来县府也派人去格罗鼎部落,部落头人心虚,以为叛乱的事情暴露,便自做主张,强先下了手,不仅扣下了来人。还派人去攻占县城外围的赤万专员公署,公署没有攻占下来,视为机密的消息却暴露无遗。李迅予得此消息,大声叫骂,却又不得不亡羊补牢,派人去各处通知:立即行动。 平静的草原变得一片惊恐,人们终于知道了没结冰的桑林湖预示的是一个怎样的灾难。 但即便如此,相对于驻守县城的解放军来说,李迅予还是颇有优势。 虽然土匪众多,但解放依仗石墙坚固,县城地形高的优势,有效发挥火力,使叛匪的进攻频频受挫。同时,县府还秘密将县基干大队队长王中及几个顽固分子关押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内部情绪,使解放军士气一直很好。 卓玉被达旺安置在山中指挥部里,每日怀着对孩子和梅吉无尽的担忧,心事重重地过日子,她已经两天没有见到达旺了,可她从周围阴郁沉沉的人们的脸上知道情况已经很不妙了。 为什么要把本来平静的生活搞乱?为什么要彼此过意不去?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为什么在死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之后,还不能停止这场可怕的错误? 卓玉变得从未有过的沉默和忧郁。 这天晚上,指挥部人声鼎沸,原来是李迅予正在指挥士兵搬运第二批空降物资。这一次空降物资有:机枪8挺、六零炮6门、子弹8万发、手榴弹40枚,同时空降的还有一名陆军少校。这位名叫王学祥的少校一到,便向他迅予、达旺等人吹嘘,美国将空运一批新式武器,装备黑水部队,派他来正是为了将来教他们如何使用新式武器。 王学祥的一派胡言,使李迅予得意忘形,一改败将的缩头缩脑,变得虎视眈眈,为了鼓舞士气,他决定当众处决几个赤色分子。 人质被统统拉了出来,绑在树杆上。倚着跳跃的火焰,卓玉在这群污头秽面,伤痕累累的人质中,找到了已经似人非人的林浩基。 天哪!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到底做了什么?要让这群人这么对待他,而且这群人中竟然也包括自己的丈夫,想到这里,卓玉的心就神经质地跳了起来。 这时候的李迅予酒过三杯,只见他站了起来,走到人质的身边,一个一个地打量,然后随手指点,“他、他、他”被点着的人质立刻被拉了出来,绑在了栓马桩上。一个刽子手用尖刀一个一个地挑开了他们的脑门,灌进酥油,然后塞进一根细松木作灯芯,人质们痛昏了过去,又被冰雪擦脖子弄醒。 “点天灯!”李迅予残忍地下令。 而她却固执地拽住了他的手,一言不发地看了他很久。 他被她的愤怒和哀凄惊愕了,而她将头埋在自己的胸前,一种压抑已久的啜泣挣脱她的意志,冲口而出,她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越哭越悲哀。 与帐外叛匪们肆无忌惮的狂笑相比,卓玉的哭声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哀哀凄凄细弱的哭声,穿透了达旺的胸膛,击碎了他的功利虚荣,擦亮了他的眼睛……一个男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哭泣声中,再次重新地申视了自己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原本有那么多的缺点,那么多的肮脏,那么多的尘埃。 “你要我怎么做?”在一声触及心灵哀叹之后,达旺沉沉地问。 可是,除了一声高一声底的抽泣声,并没有任何声音来回答他。这使他觉得自己即可悲又孤独。这一刻,他确实感到了痛心疾首,而卓玉还在没完没尽地哭着,好象要把这些日子来压在心头的哀伤和委曲都倾泄出来,那满是创伤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可以痛苦嘶嚷的机会。 帐外渐渐安静了下来,但远处却依旧断断续续地传来狂笑和诅咒声,这毫无疑问是掷髂子引起的。 终于,精疲力尽的哭过之后,卓玉缓缓地抬起了悲哀得近乎于麻木的头,恍惚地身四周看看,却见达旺正死死地盯着自己。于是,她便不由自主地向身后挪挪,恐惧极了地看着他,再次从颤抖的双唇间挤出几个可怕的字:“你是刽子手。” 她的话让他的心悲哀地一叹。 “你要我怎么做?”他急切地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然而,她突出其来的强烈反抗令他惊呀,她抽回她的手,速度之快如同被针扎过一般。这一回,他觉得有一股凉气顺着他的脊椎骨直往上走,一种冰冻般的感觉透彻他的浑身,她的脆弱和恐惧触动了他的心弦,她的缄默使他的悲哀无以复加。 这就是她要他做的,她要他做的原本是一件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她再次将头埋在自己的怀里,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哭,大概刚才的歇斯底里已经让她的泪流干了。而达旺在默默地看了卓玉之后,便沉沉地掀起了门帘,靴子踩在积雪上的声音越来越远。“不论怎么样,我一定要救出林浩基。”卓玉对着自己的胸口暗自决心,可是,自己真的有可能救出他吗? 这一刻,卓玉开始设想各种进入牢房的办法:给看守灌些酒,用钱收买他,或是干脆用一根木棒敲一下后脑勺……然后,把他弄回自己的帐篷,先洗洗,换上一件藏服,对了,还得先他吃些东西,可是,如果他有伤口怎么办?看来,还得准备一些药……卓玉越想越乱,丝毫理不出一个头结。突然,门帘被掀开了,达旺扛着一个麻袋走了进来,解开系绳,拖出一个人来,原来是林浩基。 “这就是你想救的人,你现在可以给他弄点吃的,换件衣服,二个小时后,我把你们送出指挥部。”话音一落,达旺掀帘就要离开。 此时的卓玉当然顾不上想得太多,她用清水洗净了林浩基的伤口,小心翼翼地,抹上药,又翻出一件达旺的藏袍,帮着他套上,然后端上一大篮肉,抓了一大碗糌粑,嘱咐林浩基慢慢地吃。 昏黄灯下,温馨泌人。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有机会向你解释照片上的事情,”时间一分一分地过,林浩基必须抓紧最后的时刻。“现在,对我们来说,照片上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卓玉微笑着,“也许有一天,我可以亲眼看见照片上的姑娘。” 其实,她的心中同样也有很多话想要对她说,她想要告诉他:他们的孩子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漂亮极了的小嘴,和一双永远也不闲着的小手……想到这里,卓玉哀哀地哭也声来,她是在为即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的可怜的孩子哭泣。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孩子是否安全? 二个小时,短短的两个小时就这么过了。 达旺回到了帐篷,“你们准备好了吗?”他飞快地看了他们一眼,“跟我来,别落下了。” 一瞬之间,幸福、感激、愉快……所有这些美好的感觉都聚在了达旺的心头,他觉得自己上了天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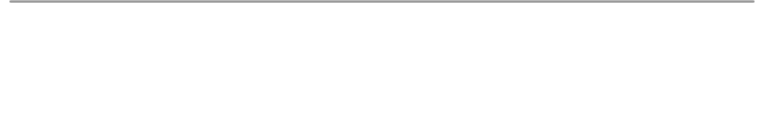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