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
1995-1998年间,我曾利用数个寒暑期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进行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我探索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族群认同」依赖其成员们对一些「重要过去」(历史)的集体记忆来维系,那么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以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记忆来凝聚认同。[1][1]
以及,我们知道当代「羌族认同」是在民族分类、识别之后才出现的,那么在「羌族认同」被建立之前,这儿各地区村寨居民的认同体系及相关社会历史记忆又是如何?关于前一问题,我曾在「汉族边缘的羌族记忆与羌族本质」一文中说明:汉族历史学者如何从中国历史记忆中建构「羌族史」,并透过土著知识分子将此历史记忆播入羌族之中;羌族知识分子又如何选择、诠释汉族与本土的社会历史记忆,建构各种版本的本民族历史以凝聚民族认同(王明珂
1997a)。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所要探讨的便是「羌族认同」被建立前这儿村寨居民的认同体系及相关的历史记忆。问题也就是:在中国历史记忆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潜藏的本土历史记忆,藉以了解「民族化」之前当地的族群认同体系?这种历史记忆以什么样的内涵组织起来,它们如何在人群中传递?如何在认同变迁中被重新诠释?如此反映的历史心性及其变迁又是如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由这些「另类历史」来了解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与历史书写的本质,及其可能的演变过程。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它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散入当今许多中国人及其边缘人群(包括羌族)之中。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它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集体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在土著中被建立起来。大部分的当今羌族说,在1949之前或甚至十几年前,他们没听过「羌族」这名词。只有羌族知识分子知道「羌族历史」(指从汉族历史记忆中建构的典范历史),[2][2]
而这些有关羌族历史的知识几乎全来自汉族的历史记忆,或是在当代汉族历史记忆框架下对本身神话传说的新铨释。但是这并不表示在现代羌族认同形成之前,在这些区域人群间从未存在某种「族群认同」,或是说他们没有「历史」。事实上在我做调查研究的期间,虽然统一的羌语、典范的羌族历史与羌族文化都在形成与推广之中,然而一些尚未完全消失的社会历史记忆,以及一些仍然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因素,使我仍然可以探索在「羌族认同」根植前的当地认同体系,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记忆——后者主要孕含在一种「弟兄故事」之中。
近十年来,在许多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历史」与人群认同间的关系都受到相当瞩目。在族群本质研究中,「历史」、社会记忆或人群间一种共同起源想象,常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的根本情感源头(Tonkin,
McDonald, & Chapman 1989; Isaacs 1989: 115-143)。在「国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历史」建构与「国族」(nation)意识产生之间的关系(Hobsbawm
1983: 12-13; Smith 1986: 174-200; Duara 1995: 17-50)。过去我也曾在一篇论文中,以社会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变迁来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与工具性本质;以族群认同的根基性而言,我认为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感情仿真源自同一母亲的同胞手足之情(王明珂1994:
125-26)。这说明为何在许多凝聚族群或民族认同的社会回忆活动中,追溯、寻索或创造共同起源永不失其吸引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认同与区分体系(如阶级、族群与国族)之中;我们因此熟悉相关的正确历史,也常常经验到「历史事实」如何被争论与一再被重新书写。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然而,在透过与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相关的「历史」研究中,或透过「历史」对人类社会认同的探讨中,「历史」都被理解为一种被选择、想象或甚至虚构的社会记忆。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近年来常见于文化或社会史中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社会记忆研究取向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之中。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是人们如何在「现在」中建构「过去」(how
the past is created in the present),也探索「过去」如何造成「现在」(how
the past led to the present)。后一研究中的「过去」不只是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以及因这些事件与人物的社会记忆而重塑的,各个时代、各社会阶层人群的历史心性或历史文化结构。
这种研究趋势,自然使学者对于「历史」一词有相当宽广的定义,也产生许多关于历史本质的争论:譬如,历史与神话的界线究竟何在?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下人们有不同的「历史心性」,因此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与述事方式?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是「神话」的述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当于「历史」?因此,文化史学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会人群的历史心性,社会人类学者探究千百里外各种异文化人群的历史心性,部分口述历史学者在主流历史所创造的社会边缘人群间采集口述记忆以分析其特有的历史心性,其目的都在探求历史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些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与边缘社会(弱势者)的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因此可以让我们藉由对自身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反思,来体察历史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他们被汉人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空间上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之间,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属于汉、藏的边缘。因此在本文中我希望透过羌族的部分社会历史记忆,不但探索一种「另类历史」,也希望藉此对「汉族」的历史心性与认同本质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在许多研究中,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与循环历史(cyclical
history)经常被用来分别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下的历史时间观念。这两种历史心性之别,或被解释为西方的与非西方的(Eliade
1954: 51-92),或被视为文字书写文化的与无文字书写文化的(Jack
Goody 1977),或是近代民族主义下的与传统的历史心性区分(Duara
1995: 27-8)。在本文中,我将以羌族的弟兄故事为例来说明一种历史心性;它既非线性亦非循环历史,而是重复着一个社会结构关系——弟兄关系——以强化人群间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的历史。另一方面,它所表达的强调人群间根基情感的历史心性,似乎曾流行于遥远的古代部分人类社会中,而至今仍残存于许多当代人群的历史书写里。因此我称之为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
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采集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县、理县、松潘,以及绵阳地区的北川等地――目前所有羌族村寨都分布在这五个县之中。部分也得于邻近羌族的黑水藏族与四土藏族(嘉绒藏族)中(见图一)。[3][3]
我选择如此广泛的田野调查范围,主要是因为我不认为有任何典范的羌族或羌族文化;了解羌族只有从各羌族人群的多元文化表征与历史记忆中探索。我也不认为对羌族的研究应受族群边界约制而限定在羌族之中;相反的,在此边界内外探索我们才能了解此边界的性质。虽然我无法走遍总数上千的羌族与邻近藏族村寨,然而本文的田野资料应已包括了深沟高山中的羌族与城镇羌族知识分子,岷江东路较汉化的羌族与西路北路较受藏族影响的羌族,羌族中的男性与女性以及不同世代的人,以及,在理县与羌族村寨相错的嘉绒藏族,以及被许多羌族认为应是羌族的「黑水藏族」。 在田野中我所问的主要问题便是:「这一群人是怎么来的?」所谓一群人,由近及远,包括家庭、家族、寨子、沟中几个寨子的集结、几条沟中所有村寨的集结、一行政区域人群、尔玛、羌族、民族(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等等。受访者包括村寨或城镇中的民众、男人与女人;受访者的年龄由十几岁至八十余岁不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整回答我的问题;然而在社会历史记忆研究中,「不记得或不知道」也有其意义。譬如,解释村寨或沟中人群共同来源的弟兄故事主要搜集于高山深沟的村寨群众之中。城镇中羌族知识虽出身村寨,然而他们常说自己从小就读书,长大后又外出工作,所以村寨中这些故事听得很少。相反的,羌族知识分子所熟知的「羌族历史」与解释所有羌族来源的弟兄故事,对村寨民众而言则相当陌生。又譬如,以下「弟兄故事」在某些地区是男女老少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在另一些地区也许只有少数老年人知晓。访问大都在几位当地人面前进行;他们有时会补充、争论,但通常会由一位被认为比较懂得过去的人代表大家述说。访问以当地的川西方言进行――这是当地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内容都以录音机记录下来,然后逐字译为文字;因此以下「弟兄故事」也是村寨民众的口述历史记忆。 从前有几个兄弟...
当今羌族约有二十万人左右。他们是高山深沟中的住民;除了在城镇中从事公职与商业者外,绝大多数羌族都住在山中的村寨聚落里。他们居住的地方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纵谷地区。村寨一般都在高山深谷之中。家庭之外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便是「寨」,现在一般多称「队」或「组」,也就是羌族知识分子所称的「自然村」。在茂县、汶川与理县附近,一片石砌的房子修在山坡上,紧紧聚集在一起,便是寨子的一般形式。几个「队」、「组」或寨子构成一个「村」,即所谓的「行政村」。一个村经常包括三、五个到近十个不等的邻近寨子。同村的几个寨子间,在婚丧、经济与宗教活动上有相当密切的往来。几个寨或几个村,又共同座落在一条「沟」中。沟,指的是从山中流出的小溪及其两岸地区;因两岸都是高山所以称之为「沟」。溪有枝状分支与上游下游,因此沟有大小内外之分。譬如,一个小沟的上游称内沟,可能有几个村(或寨);其下游称外沟,也有几个村(或寨)。这条小溪沟与其它几条小溪沟共同汇入一条岷江上游的支流之中,因此所有这些「小沟」又属于那个「大沟」的一部分。就在这些村寨中,普遍流传一些有关几个兄弟的故事。 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
当今北川地区,也就是明代著名的青片番、白草番活动的地区。明代后期大量汉人移民进入此地区,造成严重的资源竞争;这便是青片番、白草番「作乱」的社会背景。关于祖先的来源,在北川的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最流行的说法便是几个兄弟从外地来,后来便分成当地几个有汉姓的家族。有些家族说他们是松潘白羊,或茂县杨柳沟来的,以强调他们的羌族身份。另一些则说祖先是湖广,或湖广麻城孝感来的,强调他们与汉族间的联系。 1.
我们老家是从白羊迁出来的,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松潘的白羊有羌、藏、回。片口乡姓董的最多。我们组的人是各地来的...,本地人只占三分之一。五八年过粮食关,大量的人从外地迁来。砍一块地烧了,就能种东西,后来组成村。姓董的、姓王的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内沟的人三分之一是从白羊出来的。上沟原来没人...,羌族喜欢砍地烧了开荒,看到了冒烟子,亲戚都来了。人多了,也不怕野猪、猴子来吃粮食。其它的都是逃荒由外地来的。我听过原有五个兄弟从松潘毛儿盖那过来,五个人各占一个地盘;我记不清础了。 2.
小坝乡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特别我们刘家在小坝乡,最早;听我祖祖说,就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当时是张、刘、王三姓人到小坝来。过来时是三弟兄。当时喊察詹的爷爷就说,你坐在那儿吧。当时三弟兄就不可能通婚,所以就改了姓。刘、王、龙,改成龙,就是三条沟。一个沟就是衫树林,那是刘家。另一个是内外沟,当时是龙家。其次一个就争议比较大,现在说是王家。这三个沟,所以现在说刘、王、龙不通亲。三兄弟过来的...。去年我弟还挖出一片衫树,就是老大在那坐到,长期居住。 3.
我们是湖广孝感过来的,五兄弟过来,五个都姓王。主要在漩坪、金凤、白泥、小坝。这五个兄弟,两个到小坝,一个在团结上寨,一个在这里。我们祖爷是行医的,我们家还保留个药王菩萨。过来五辈了,这是五辈以前的事了。他们都不是湖广过来的,因为只有我们一家在七月十四过七月半。他们也说是湖广过来的,但他们跟我们过七月半不一样。
由以上小坝乡民众的家族记忆中看来,这些记忆相当混淆,且常互相矛盾。例1小坝报告人的记忆中,「从白羊迁出来...姓董、姓王的是同一个祖先」,说明内沟中该组两个大家族的血缘关系。然而当谈到上沟时,他便忆起在更大范围内,「五个兄弟从松潘毛儿盖那过来,五个人各占一个地盘」这样的记忆。现在内沟该村正好包括五个组;这五个兄弟是否是这五个组的祖先,报告人无法确定。
小坝乡的衫树林位在内、外沟的沟口,因此比起上游内、外沟的村民,这儿的村民对外的联系更多,更具汉族特质,以及有更多的汉族祖源记忆。例2口述中的三弟兄故事包含更大的人群范围,广泛分布在内、外沟,衫树林,以及一些不确定的人群。此种不确定性使得由此三兄弟记忆所凝聚的人群具有相当的扩延性。譬如,这个不确定的弟兄「现在说是王家」的祖先,而「王家」在当地又是大姓,因此这个记忆可能将三兄弟的后代由内、外沟扩延到整个小坝或更广大的地区。
小坝例3的口述记忆,便代表这样一个联系更广的兄弟故事。例3与例1两位报告人同寨。这儿所称的「王家」,就是例1报告人口中的王、董一个祖先的「王家」,也是例2报告人所称「三兄弟」之一后代的「王家」。但在他的记忆中,祖先不是来自松潘白羊或毛儿盖,也不是来自湖广的刘、龙、王三兄弟,而是来自湖广孝感的王姓「五兄弟」;来此后分散到包含小坝的更广大地区。这个记忆不但凝聚小坝的王姓家族,也让他们得以与更大范围的北川各乡王姓家族联系起来。
在此我们必需说明,「湖广填四川」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四川人中的历史记忆。故事是说,当年流寇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得只剩一条街的人,所以现在的四川人都是从湖广绑着迁来的移民,而且所来自的地方都是「湖北麻城孝感」。不只是许多较汉化地区的羌族宣称祖先来自湖广,在四川的汉族中这种祖源记忆更普遍。从前或真的有一些移民从湖北麻城孝感来到四川(孙晓芬
1997),但以目前此祖源记忆在四川人中普遍的程度来说,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其中大多都是虚构的家族起源记忆。
明代「白草羌」的大本营,北川的片口乡也有许多类似的兄弟故事。 4.
听他们说这的羌族都是从杨柳沟、小姓沟、夹竹寺搬来的。最早搬来的杨家,搬到来寿,那里长的树,衫树,把那开垦出来。原来还分上寨子,中寨子,下寨子......。那还有三棵大柏树,三棵长在一起。说是杨家来时是三弟兄,为了纪念他们来,就种了三棵柏树。 5.
我听说,大概有三百多年了,明朝末期,清朝初期,从茂汶县的杨柳沟。当时估计都是打猎为生。我们还不是最早的,听说最早是田家。过后,我们打猎走走走就过来了。我们过来先帮田家做事。传说是,我问过很多人都没有准确的说法。听说是,过来好象是一家人,儿子没过来完,那边也有。从武曲上五村那翻过来,在那边也有;过来只有一个,一个幺娃子,就在这定居......。听说最早来的是三弟兄,三棵树子,这都是听说的。
例4报告人说杨家三兄弟最早来这儿。但在例5中,一位杨家的人,虽然他也承认听过三位杨家兄弟的故事,却说只来了一位杨家人。他认为其它的杨家兄弟祖先在青片、茂汶,如此杨家与当地典型的羌族(青片羌族)或核心的羌族(茂汶羌族)有更密切的关系。[4][4]
但他的口述中更真实的应是:「很多人都没有准确的说法」。
这样不确定的「兄弟故事」也存在于青片河上游的上五寨。 6.
我们乔家的家谱说两弟兄打猎来到这,看到气候好,野猪挖出来的土看来也很好,就把帽子、帕子上的一点青稞撒下,说明年青稞熟时来看那边先黄。结果这边熟得还要早些,于是搬来这里。两兄弟原在一起。后来分成两个地方,现在还有分是老大的还是老二的后代。我们是老大的后代。老人还说原来有四弟兄,事实上来的是老三、老四,其它兄弟在茂县。这说法现在看来是合理,那边的人辈分高。前几年茂县较场有人来这儿。
报告人认为茂县「那边的人辈分较高」,是因为北川各羌族乡成立较晚(最晚的在1985-86才成为羌族乡),且北川羌族中几乎已无土著文化遗痕。这种认为北川羌族辈分较低的看法,也表现在一个扩大的「兄弟故事」之中。 7.
我现在听说羌族过去是个大的古老的民族,在黄土高原被打败了,西迁,后来一小支转到岷江流域来。当时那住的是戈基人。打败了戈基人后才住在这里来。我听说,当时有九个儿子,北川是老九,叫而贵,分到北川这来。其余都在那边,只有老九在这儿。这在冉光荣的《羌族史》中有。我们常说我们是老九的后代。 8.
阿爸白茍有九个儿子,这故事主要在茂县那。他由青海迁到岷江上游,遇到戈基人,但戈基人事实上是羌族的一支。阿爸白茍率领一只大部落到这来,跟戈基人战争,始终打不赢戈基人。后来就有天神来当裁判,但他帮羌族,就用白石头给羌族,给戈基人发的都是软的东西。最后阿爸白茍就把戈基人打败了。他有九个儿子就分到松潘、黑水、茂县、汶川、北川、理县、灌县;其中第九个儿子分到北川,第八个儿子分到灌县...。这故事我是从资料上看来的。羌族资料主要由端公来传承,有上坛、中坛、下坛经,其中,上坛经都是人是怎么来的,这一类的。
这两位报告人虽然分别出身于小坝与青片,但都是长期在北川县治曲山镇居住、工作的羌族知识分子。在这个「阿爸白茍的九个儿子」故事中,他们都说北川羌族是九弟兄中老幺的后代。这个兄弟故事的流传有多重的社会意义。首先,这故事我在茂县、汶川、理县各沟各村寨的田野采访中都很少听过;目前这故事似乎主要流传在城镇羌族知识分子之中。阿爸白茍与戈基人的故事的确保留在羌族祭师端公的经文之中,但端公目前几乎已消失殆尽。即使有少数朔果仅存的端公,村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唱词(一种据说是较古老的「羌语」)。事实上「阿爸白茍的九个儿子」故事,是羌族文化工作者与汉人民族研究者由端公唱词中译成汉文,然后以「羌族民间故事集」等形式发表。因此能读汉文的羌族,关心羌族文化的羌族知识分子,才能够将这个故事说得完整。村寨中的羌族农民反而不知道这故事。
其次,以上报告人有关「阿爸白茍九个儿子」之说,来自罗世泽采录的「羌戈大战」故事。在此故事中,阿爸白茍九个儿子所占居之处为:格溜、热兹、夸渣、波洗、慈巴、喀书、尾尼、罗和、巨达。这些「乡谈话」中的地名,在罗的译注中分别对等于茂汶、松潘、汶川、薛城(理县旧县城所在)、黑水、棉箎(汶川旧县城所在)、娘子岭(映秀旧名)、灌县与北川(罗世泽
1984)。这些地区包括羌族知识分子的「民族知识」中五个主要羌族分布县(茂汶、松潘、汶川、理县、北川),以及他们的「历史知识」中过去羌族曾分布的地方(娘子关、灌县),以及他们的「语言知识」中其居民应为羌族的地方(黑水)。而在其它版本的「羌族民间故事」中,羌戈大战之后并非阿爸白茍的九个儿子分到茂县、汶川、理县、北川等地,而是木比塔(天神)命有功战士到北由松潘、黑水南到理县一带(不包括北川)的著名沟寨中定居;这些沟寨如,松坪沟、黑虎、坝底、三溪十八寨、大小二姓、九枯六里等等(阿坝州文化局
n.d.: 26-27)。这些沟名、寨名与联合地名,代表本世纪上半叶分布在茂县、汶川、理县岷江西路部分沟寨民众最广泛的「我族」概念。如今在罗世泽的版本中,这故事如其它的羌族弟兄故事一样,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前国家民族区划与行政区划下的羌族概念。这故事不同版本间的变化,也显示诠释、传布这故事的人由端公变成羌族知识分子;故事的传递由口述而成为口述、文字记忆并行;故事由说明各沟各寨人群的共同起源,而成为当前几个行政区(县)中羌族的共同来源。这都是「羌族」认同形成中的一些变化现象。
最后,阿爸白茍的九个儿子分别到茂县、汶川、理县、北川等地的说法,在茂县、汶川等地羌族知识分子中较少被传述,而北川羌族知识分子对此说比较有兴趣。这应是由于北川与其它羌族地区以大山相隔,分属不同水系;北川的土著语言、文化早已消失殆尽。这些因素使得北川羌族处于羌族认同的边缘而有深切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使得他们特别需要强调本地羌族与茂、汶地区羌族的同源性。 茂县永和村
由北川青片乡西向越过土地岭梁子,便是岷江流域的茂县永和乡。永和村各寨的人深处岷江东岸支流之中,在清代时已成为受中国官府管辖的「羌民里」。这儿的人从前被岷江边渭门一带的人视为「蛮子」,而永和各村寨的人则视下游渭门的人为「烂汉人」;现在则两地的人大都自称羌族。永和村各寨中也流传着兄弟故事。 9. 我们是搬来的。老家是渡基。那边地硬得很,一般的娃儿不说话,哑巴。一个传说,背到这个梁子这,听到老鸦叫,学老鸦叫就会说话了。过来时就只有我们那一组人。走到那老鸦叫了,娃儿就说话了。这边几个组几乎都是那来的。这儿原来没有人,根根是这样扎的。渡基是高山,两弟兄,大哥在渡基,兄弟到这来。现在又搬一些人回去了。原来那已没有人住了。垮博(一组)跟这里的人(二组下寨)是从那来的。 10.
我们一组也说是渡基那迁过来的。我们也说走到金个基那个梁梁,小孩听到老鸦叫就学老鸦叫,听到狗叫就学狗叫...。他们说上寨是大哥,就是得牛脑壳。一队得的啥子?三组是得牛尾巴,道材组得的是牛皮子。他们现在骂三组就是骂你们是牛尾巴;道材组被骂夏巴,夏巴就是牛皮子。上、下寨都是二组,我们得牛脑壳。
这个村目前包括四个组,其中二组又分上、下寨。永和例9报告人的版本中,一组、二组同出一源,他们与渡基的人是「两兄弟」的后代。现在一、二组大多数的人都同意永和例10报告人的版本。这说法是「三兄弟」来到这儿;得牛头的分到二组上寨,得牛尾巴的分到三组去,得牛皮的到四组去。一组与二组下寨则由二组上寨分出来。另一个版本得自于一位87岁的一组老人,他说「三兄弟」是分别到一组与二组的上、下寨;一组得牛尾巴,二组上寨得牛头。他的说法与例9报告人(六十余岁)的说法,事实上都在强调一组与二组之间的密切血源关系。
在以上的口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弟兄故事」在各世代人群间的争议性与可塑性。老一辈村民的认同中,只强调一组与二组的「同源」;当新世代村寨居民的认同圈扩大时,当今中年辈村民将「三兄弟」扩张为四个组的共同祖先,四个组的人都是那些兄弟的后代。一组与二组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代,如此认同圈虽扩大了,但一组与二组的人仍宣称彼此有特别紧密的同源关系。目前在祭塔子(祭山神菩萨)的习俗上,一组、二组共同敬一个塔子;三组、四组各有各的塔子。而四个组共同祭的只有「东岳庙」。当地祭塔子、庙子的习俗与「兄弟故事」两者呈现的认同体系与世代变迁是一致的。 茂县三龙地区
三龙乡位于岷江西路支流黑水河的一条小支流中。该乡各村寨在清代中晚期已改土归流。而且,这是清代受中国政府能够直接管辖的最西方「羌民」村寨;再往西或往北去,从前都是地方土司豪强的势力。我所探访的村寨中,只听得一个兄弟故事。 11.
我们这队最早是部落时代,这边属牛部,那边是羊部。牛是哥哥,兄弟,我们归大朝(按:
指清朝中国政府)早些。我们牛部,大的范围宽得很。我们唱酒歌从松潘唱下来;先唱松潘,再唱黑水。据老年人讲是两弟兄,我们比那边牧场宽些,那边窄闭点,两个人就住在这一带。两兄弟,弟弟过黑水河查看地盘。后来就安一部分人往那迁。过后兄弟安排好了,就来邀他哥过去。过去看他的地盘。就要跟他哥分家,他哥哥不干;弟弟想独霸一方,哥哥不干。弟弟跟他的人就把哥哥打了一顿。哥跑回来,不服,又把他兄弟弄过来,说我跟你分,结果又把弟弟砸了一顿。现在我们老人还说先头赢的是「掐合」赢。锤打了,那我们就分开;那边就是羊部,这边就是牛部。白溪那以下我们都喊「掐合部」,我们这就是「瓦合部」,以黑水河为界。我们说黑水河那边的人狡得很。
在这故事中,报告人认为隔黑水河对望的两岸各村寨是有敌对关系的兄弟。一个勒依寨的老人也说掐合部、瓦合部常打来打去,他不知道这是两个兄弟;但他的同寨后辈(中年辈)则说掐合部、瓦合部是兄弟。位置更高的诺窝寨中,报告人则说没听过掐合部、瓦合部。 松潘小姓沟
松潘地区是阿坝州羌族分布的北界,而松潘镇江关附近的小姓沟正在羌族、藏族错居的地方。从前镇江关一带的人称小姓沟人是「猼猡子」——会偷会抢人的蛮子;小姓沟的人则称镇江关人是「烂汉人」。目前小姓沟有羌族也有藏族村寨。镇江关则是藏、羌、汉、回混居。这儿的羌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远较其它地区的羌族为低。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居住、穿著上与附近的热务藏族相似。我所采访的村寨,埃期村,是这条沟中最深入大山中的一个村寨;当地居民的汉化程度又比同沟中其它村寨的人为轻。这儿的村民们,除了少数出外读书的年青人外,大多没有汉姓。这个村目前由三个组(白基、白花、洁沙)构成;二组又分成白花与梁嘎两个小寨。在这儿,「兄弟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然而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在这里即使是十来岁的小孩都知道这三弟兄的故事(例13的版本)。 12.
埃期传说一开始有三弟兄分家,分到三个地方。在我们房子上方,原来就在那儿。现在有六户人,失火后就没人住了。过去传说三弟兄中在那儿留了一个。河坝头那边一个山头住一个兄弟。另一个就在一组的地方,就这样发展起来。还一种说是挨期五寨,包括一组、白花(二组),一组斜过去,嘴嘴上有一个寨子。三几年红军长征时,得一次疟疾,痢疾,人都死光了。 13.
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弟兄,大哥是一个跛子,兄弟到这来了,还一个幺兄弟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太阳晒得早。幺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儿来埋。 14.
一组的人,以前是三弟兄来的。以前这没得人,三弟兄是从底下上来的。上来坐在月眉子那个敦敦上。又过了一两个月。那个就是,不是三弟兄喔,那是九弟兄,九弟兄占了那地方。三弟兄打伙在这条沟。还有两弟兄打伙在那条沟,大尔边。还有两弟兄打伙在大河正沟,热务区。九弟兄是黄巢,秦朝还是黄巢?秦朝杀人八百万?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就躲不脱了,就走到这儿。一家九弟兄就到这儿来了。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 15.
七弟兄,黑水有一个,松坪沟一个,红土一个,小姓有一个,旄牛沟有一个,松潘有一个,镇江关有一个。五个在附近,迁出去两个;一个在黑水,一个在茂县。埃期是三弟兄分家,老大在二组,老二在三组,老三在一组。三弟兄原不肯分家,老大出主意,以后我们去世了我们三个人还是一个坟堆,就是二组的那个坟堆。
在以上四例的口述中,「三兄弟故事」说明目前这条沟中三个寨的祖先来源;这是当前这儿最普遍的社会记忆。例12中报告人提到另一种说法,原来当地有五个寨子,其中之一在三十年代因疫疾而灭绝。据说人已灭绝的寨子残迹还在那儿。这个说法应有几分真实。民国十三年修的《松潘县志》中记载,略位于小姓沟埃期附近的寨子有:柴溪寨、纳溪寨、白茫寨、白柱寨、料杠寨、背古楼寨等六个寨子(傅崇矩
1924: 4.36)。经与数字报告人查证后得知:白柱即目前的一组白基;白茫应为白花之误,即二组;料杠即梁嘎,是二组的上寨;柴溪是三组;其它两个寨子不清础。虽然无法证实在三十年代红军过境时这儿真有五个寨子,但在过去此处的确不止三个寨子(二组是将两个寨子合在一起形成的)。因此「三兄弟分别为三个寨子祖先」的故事,应是在近五十年来被创造或修正出来的记忆,以符合目前只有三个「组」的事实。
例13报告人说了同样的三兄弟故事,但说得更详细。这也是目前所有三个组民众间最典型与最普遍的说法。在这故事中,老二与老三关系格外亲密;不只住在同一边,死了也葬在一起。目前三组在阳山面(早晨晒得到太阳),一组与二组两寨座落在阴山面。这个兄弟故事所显示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也表现于三个组敬菩萨的习俗上。三个组都各自有自己的山神菩萨;二组上、下寨也有自己的菩萨。二组下寨(白花)又与一组共敬一个菩萨,「忽布姑噜」。三个组共同敬的大菩萨就是「格日囊措」。因此,据村民说,因为一、二组同一个菩萨,所以常联合和三组的人打架。
例14中报告人也说「三兄弟故事」,不同的是,他说埃期这三兄弟是九兄弟的一部分。九兄弟中,事实上他只提到七兄弟的去处;三个到埃期,两个到大尔边,两个到热务。「两个到大尔边」可能指的是,在大尔边那条沟中实际有两个大村:大尔边与朱尔边。[5][5]
热务与大尔边是埃期的左右紧邻。在目前的民族分类中,热务居住的是说热务藏语的藏族;大尔边、朱尔边居民则是羌族,语言与埃期的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因此这个「九兄弟故事」扩大了以「三兄弟故事」来凝聚的埃期三寨认同。而且其所孕含的人群认同范围,打破了目前藏、羌间的边界,这一点相当值得注意。[6][6]
例15报告人首先提到的是「七兄弟的故事」,这七兄弟故事涉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这些地区人群,以目前的民族与语言分类知识来说,包括有红土人(热务藏族),小姓沟人(藏族、羌族),松坪沟人(羌族)、镇江关人(汉化的羌族、藏族与汉人)、松潘人(以汉族、藏族为主)、旄牛沟人(藏族)与黑水人(说「羌语」的藏族)。在这样的兄弟故事记忆中,由于小姓沟所有村寨的人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代,因此「小姓沟人」认同得到强化。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七兄弟故事」强调一个以小姓沟为核心,跨越茂县、黑水、松潘三县,包含许多村寨与城镇藏、羌族群的人群认同。这个人群范围,也就是小姓沟人经常能接触到的、与他们共同祭「雪宝顶」山神菩萨的人群。这位报告人早已迁出村寨,住在小姓沟羌、藏村寨居民出入门户的「森工局」。这是一条总共只有十来家商店、住宿处的小街市。运木材的卡车司机在此休息过夜,沟内各村寨羌、藏年青人也喜欢在此逛街吃喝。这或许是报告人强调「七弟兄的故事」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另一方面,他说「老大在二组,老二在三组」,与当前村寨民众的说法(见例13)也有出入;这也是一种社会失忆。 理县杂谷脑河流域
杂谷脑河流域的理县,县城中羌、藏杂居。羌族村寨则分布在县城东边甘堡以下;往上游去便都是四土人(嘉绒藏族)的聚落。这一带羌族村寨常与四土人村寨相错,因此他们与四土人有相当密切的往来关系。这儿的羌族常自称五屯的人,因为他们多在清代当地五支屯兵中九子屯的调兵范围内。沿杂谷脑河的大道是入藏或进入川北草地的一条孔道,自古以来便有中国官府驻防,以及有汉人来此经商,因此这儿的羌族与藏族都有汉姓。但除了接近河坝寨子的人外,一般很少有人称本家族是「湖广填四川」来的。这儿的村寨中,也经常有「同姓兄弟故事」,而且愈偏远的寨子里愈普遍。 16.
我婆家的邹是三兄弟到增头,约十二代,分成三家邹。有一个祠堂,有一个总支簿,人那里来那里去,后来几个小孩子造反派把它砸了。以前的墓碑好看,有石狮子,还刻了字,人那里来那里去都有...。姓邹的三弟兄,不知是那一个分到铁甲,那一个是铁盔。银人这个根根没有人了,盔甲这支人多。 17.
我们杨家最初是从外面上来的,我们的杨是大杨;杨有小杨、大杨,有角角羊。以前有几弟兄,有下堂的是小杨,没有下堂的是大杨。下堂是到别人家上门的。下堂的后头坐,没有下堂的先头坐......。两弟兄来,一个下堂,分成小杨、大杨;那来的不晓得。 18.
木达姓杨的多,一个家族有十多家......。据说古代我们没有姓,和米亚罗这一带一样。老人家说是由房子的名字推出来的,譬如房子在下面就姓夏。从民族来看百分之百都是藏族,所以古代没有姓......。我家来时有三弟兄,四、五百年前从那来不清楚;两个在木尼,还有一个在这儿,杂谷脑附近。据说以前有一个姓杨的员外,几个弟兄中,我们家是大哥,弟弟分出去,所以我们是最早的。
以上例16与例17中的报告人是羌族,例18报告人是嘉绒藏族。他们的「兄弟故事」将一些同姓人群联系在一起;这些同姓的家族不一定在同一村寨之中。虽然宣称祖先有弟兄关系,但在以上三例中,报告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些同姓家族支系间的区分与优劣阶序。
除了村寨中各姓家族的弟兄故事外,本地还流传另一种「兄弟故事」,这种「兄弟故事」将更大范围的人联系在一起。 19.
白哈哈、白西西、白郎郎,他们是三弟兄,出生在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古羌贵族。但听说周围有很多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就把家财卖了,带了财富离家,沿途救济,最后就在白空寺住下来。白空寺就是天彭山顶。三兄弟,一在白空寺,一在铁林寺,老幺白郎郎在天元寺。他们没有后代,他们当菩萨去了,没有后代。 20.
薛城有些老人说,薛丁山打仗在此打了胜仗,以此命名。我查了其它的资料,就不是像薛城的人说的。阿爸白苟有九个儿子,其中的老四就到了薛城。阿爸白苟――羌语不好翻――他后来又有九个儿子,九子。他好象也是青海来的,地名移到这儿来。
过去白空寺中的白空老祖是当地「四土人」(嘉绒藏族)、「尔玛」(蒲溪沟的人除外)、汉人共同信奉的菩萨。目前,在有些当地羌族知识分子的口中,白哈哈、白西西、白郎郎与「羌戈大战」以及羌族的「白石神」等文化符号联系在一起,并搀杂中国古代黄河上游羌人的历史记忆,而成了来自黄河上游代表理县羌族的神。虽然例19报告人不认为现在那些人群是这三位菩萨兄弟的后代,但由于三位菩萨分别供奉在三个地方的寺庙中,因此他们的兄弟关系也将他们的各地村寨信徒们联系起来。对于村寨里的人来说,他们大多只知道「白空老祖」,而不知这三兄弟的故事。 例20中报告人所说的「阿爸白茍九个儿子的故事」,是将理县羌族与茂、汶、北川等地羌族联系起来的同源记忆;同样受到汉人西羌历史记忆的影响,这个祖源被认为是「青海来的」。过去当地老年人以汉人历史记忆中之薛丁山来解释「薛城」地名来源;此报告人不以为然,他以「阿爸白苟的九个儿子」解释「九子屯」地名之来源。这也表现了在「汉化」与「羌族化」不同的历史意识下,人们对于当前地名有不同的铨释。
理县蒲溪沟各村寨人群,从前在杂谷脑河地区是最被歧视的。河对面各村寨中自称「尔玛」的羌族人,称这儿的人为「尔玛尼」(rmani);以现在的汉语来说就是「黑羌族」。阳山面的羌族以他们的地较好,过去又属于可被土司征调作战的「五屯」,因此对于「作战时只能背被子的尔玛尼」相当轻视。过去他们宁愿与同属「五屯」的四土人结亲,而不愿与这儿的人结亲。他们认为,蒲溪沟的人许多都是外来的汉人,而蒲溪沟的人也常自称他们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或是崇庆州来的;而来此的又经常是「几个兄弟」。 21.
我们王家是湖广填四川时到这来的。在灌县那一个石堰场,先迁到四川灌县石堰场。湖广那里就不知道了。五弟兄到这里来,生了五弟兄,分成五大房,我们还有家谱。湖广那里我不清楚,家谱上有记......。这几个寨子的形成。听说是原没有枪,是用箭。箭打到那里就在那里住。几个兄弟分家时,箭打到那就在那住。这三个弟兄不知从那来的;一个是蒲溪大寒寨,河坝的老鸦寨,还有色尔,这三个是最早的。传说是这样。 22.
我姓王,祖先住休溪,有五代人,转来又九代。休溪王家有五大房,是五弟兄分家出来的。五弟兄,以前我们的排行是「万世文泰杰庭臣凤国明」。五弟兄在此之前,传说是张献忠剿四川,从湖北来的。不肯过来,背着手被押过来的。所以四川人爱背着手。搬来再到石堰场。有三弟兄,一个来这里,从湖北麻城孝感来四川。这是老人在摆的。 23.
孟姓在这有八家,其它姓王的最多,再有是姓徐的。姓孟的有七、八代了,我们徐家十多代了,崇庆县出来的。那儿有一个徐家寨,人太多了就分出来了...。王家是外头进来的。徐、孟、余三姓安家时是三弟兄,原来是一个姓,现在三姓都不准打亲家。原来是三弟兄分家下来的,祖坟都相同的,到这儿来分家的。孟家也是外头,崇庆县过来的。王家不是,他们来得早。开坛时就唱「阿就」、「王塔」;「阿就」是姓王的,「王塔」是三姓。 24.
「尔玛」那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羌族好战,好战就要占高位子。老年人说,老鸦、蒲溪、色尔是最早的。那时好战,从黑水几弟兄出来,三弟兄出来。好战,用麻杆杆打战,还是,我记不得。逃到山上,居住山上,这三处占得高,色尔、蒲溪、老鸦,好放石头防守。黑水叫
zum 河。都觉得自己找的地方相当好。蒲溪就是「北吕」,面堆起的尖尖;老鸦是老鸦飞得的地方;色尔我就不知道了。
例21中报告人说了两个故事:一是「五兄弟」,这是休溪王家五大房的由来;一是「三兄弟」,这是蒲溪沟最早三个寨子居民的来源。例22报告人是前述报告人的父亲。他的说法则是:由湖北麻城孝感来的是三弟兄,其中之一迁到灌县石堰场,然后他的后代有五兄弟来到蒲溪的休溪寨。我抄录了这一王家的家谱;这是一个号称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世居于四川省中部资阳与简东的王姓家族族谱——里面找不到这五弟兄或三弟兄的痕迹,也找不到与休溪王家的任何关联。
例23的报告人称,休溪徐、余、孟三姓人的共同祖源是由崇庆县迁来的「徐姓三弟兄」。但他也说,开坛时要唱「阿就」(王姓)、「王塔」(徐、余、孟三姓)。羌族人在开酒坛念祭词时,所念的是大小菩萨及寨中的各家族祖先神。因此,这有可能是外来汉人因入赘而祭当地之地盘神,但更可能是当地家族使用汉姓及虚构汉人祖先来源。由于他们所持有的汉姓族谱与口述中的汉族家族记忆几乎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当地人假借汉人祖源的可能性较大;由湖广迁来之说应是虚构的。关于「弟兄故事」中涉及的是神话或是史实此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例24中所说的「三兄弟」与例21中的相同;这是在蒲溪沟中最普遍的兄弟故事。由于当地人认为,现在蒲溪五寨是由最早的蒲溪、老鸦、色尔三寨分出,因此这个「三弟兄故事」也说明了蒲溪各寨的共同来源。但说到各家族的来源,则许多家族都说自己是外地来的汉人。当地许多人一方面宣称本家族的「汉族诸弟兄」来源,一方面强调本寨的「黑水三兄弟」来源;对他们来说这中间似乎并没有矛盾。无论如何,家族与家族之间,或寨与寨之间,都以祖先的弟兄关系来凝聚。「黑水来的三弟兄」此一共同记忆无论是否虚构,其另一意义便是以「蛮悍的黑水人后代」,来抗辩阳山面的人认为他们在打战时「只够资格背被子」的说法。 黑水
芦花镇以东的黑水地区,主要人群是所谓「说羌语的藏族」。他们说的是与赤不苏区羌族类似的语言,在语言学家的语言分类中属于「羌语」。他们以本土语言自称「尔勒玛」;与赤不苏、松坪沟、埃期沟的羌族自称类似。在宗教上他们一方面是藏传佛教信徒,另一方面其屋顶上置白石的习俗,以及山神信仰都与东邻赤不苏一带的羌族类似。五十年代前后,本地土司头人与西方马尔康一带的嘉绒藏族土司,以及北方草地各游牧部落头人们来往较密切;嘉绒藏语是土司头人们的「官方语言」,而黑水人在节日中穿著的盛装服饰也接近嘉绒服饰。相反的,东方(黑水河下游与岷江主流)各村寨人群则对他们既憎恨又畏惧。在从前,当地汉语中的「猼猡子」主要便是指野蛮的、会偷会抢的黑水人或特别是小黑水人。黑水河中下游一带「乡谈话」(所谓羌语)中的「赤部」指上游的野蛮人,而黑水人又被认为是典型的「赤部」。连前述小姓沟的人也称这儿的人为「猼猡子」。这些,或许部分说明了为何黑水人在民族识别中被划分为藏族。 事实上在过去,与「羌族」的情况相同,这些「说羌语的藏族」内各次群体彼此也不相互认同。虽然所有这些地方的人都自称「尔勒玛」(口音有别),但西方红崖的人称下游维古的人为「日梳部」,更西方的芦花人则称红崖的人为「日疏部」。维古的人则称红崖人为「日基部」,红崖人则称上游芦花人为「日基部」。介于红崖与维古间的麻窝人,则认为由红崖到麻窝都是「尔勒玛」;芦花人是「日基部」,而「日疏部」则是维古与石雕楼的人。再者,所有芦花、红崖、麻窝、维谷的人称小黑水人「俄落部」;小黑水人则称黑水河的人为「赤部」。而所有小黑水人与黑水人,都认为下游茂县各沟(赤不苏、洼底、三龙、黑虎等)村寨人群――也就是后来的羌族――是「而」(汉人)或「啷」(汉人不像汉人、民族不像民族的人)。坚决认为「尔勒玛」与下游的「啷」不同,也使得今日绝大多数黑水与小黑水人都认为「尔勒玛」就是藏族――包括由芦花到色尔古、石雕楼以及小黑水的人――,而与下游的羌族毫无关联。然而在接受语言学家的「语言分类」知识,以及认为语言与民族间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分类」知识后,目前羌族知识分子普遍认为黑水人应是羌族。相反的,自认为是藏族的黑水知识分子则努力推广藏语文教育。
与羌族地区比较而言,在这儿很难采集到有关一群人的「共同起源故事」,包括「弟兄故事」。但由以下的口述中可以知道,这种联系几个家族或几个寨子的「弟兄故事」是存在的。 25.
我们那有姓杨、姓王的,有些家一代代传下去,有些随便喊。我不知道姓杨的那来的。只知道亲戚很多。只听到牛脑壳、牛尾巴,几弟兄那个分到牛脑壳,那个分到牛尾巴,就到那去。 26.
「阿察克」怎来的不知道;都是一个菩萨,就是神龛的名字。一个寨子才有塔子,家族没有塔子。我们有更大的――就像是中华民族分成许多民族――,我们有更大的家族,分成几个小族。家族不一样,但搞丧事大家要一起搞。一个家族,常几弟兄分开了,就分成几个家族。
小黑水是黑水河的支流,这儿的人在语言、文化习俗上都与黑水人有些差别。从前,下游赤不苏人认为黑水人落后、野蛮,是「猼猡子」。然而在黑水人眼中,真正落后野蛮的「猼猡子」则是小黑水人。在清代与民国初年的地方志中,这儿的族群的确被记录为「猼猡子」。到了民国时期,「猼猡子」还被认为是一个特别的民族(Torrance
1920;陈志良
1943: 39)。在小黑水近河坝的村寨中,有一些人宣称他们的祖先原是汉人,而且这些有汉姓的家庭,也经由「几个兄弟从外地来...」这样的记忆来说明彼此的血缘联系。在山上的村寨中,则有祖先为从草原来的几弟兄的说法。 27.
解放前,况而河坝与知木林河坝原来比较早进来的都是外来的。像我们原来姓杨,后来就不用汉姓了,都用藏名。我们的祖祖是安岳人,做木工的。就在况而河坝,还有几家。况而河坝原有三家人,三家人都是从外面进来的,都是汉族。 28.
我们王家是安岳来的,祖婆是本地人,祖祖是外地人。安岳出木工,出来了一大批人。几个弟兄到了一个山上。插了麻尼旗旗,今天插,明天看自己的旗旗往那倒就到那去,因此就散了,一个沟沟去一两个兄弟。我们的祖祖到晴朗,后来跟我爸爸又到这来。我们姓王,他们姓杨,都是一个根根,几个兄弟一起来的。(例31报告人)可能是结拜弟兄,大家出来不方便,结拜弟兄可以互相照应。进来一伙人,这儿人稀少,就听天由命,插竿竿。一个王家、一个杨家,还有就不记得了。姓都不一样,肯定是结拜弟兄。
上例27报告人是在县城工作的当地知识分子;例28报告人则是小黑水老人。在这位知识分子的家族回忆中,并没有提及「几弟兄」的故事;即使听老人说这些住在河坝的家族是几个汉人弟兄的后代,他将之铨释为「几个结拜弟兄」。这个例子也说明,新「知识」与「理性」如何使得当地的「弟兄故事」逐渐消失。 从前松潘、热务、黑水、红原一带有「察合基」与「博合基」之分;他们用汉话说,就是羊部落与牛部落。在松潘小姓沟,这是渐渐消失的记忆;很少人知道牛部落与羊部落究竟是什么。在三龙乡,前面我们曾提及,这两种人(掐合部与瓦合部)被说成是两个敌对兄弟的后代,分别居住在黑水河的两岸。同样的,知道这种区分的人不多,而且能说这故事的人也认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在小黑水地区,「察合基」与「博合基」仍是鲜活的记忆。而且,到现在属于不同集团的寨子还认为对方坏、狡滑。据他们对「察合基」与「博合基」的描述,可以看出这原是藏传佛教两大支派所造成的村寨间区隔。 29.
我们是「察合基」,羊部落,就是「麦子」。「博合基」就是牛部落;牛脑壳是「麦尼」。乌木树、热石多、卡谷、卡隆镇,都是「察合基」。杀了羊之后就把羊脑壳在房子顶顶上搁到。「博合基」,牛部落:晴朗、知木林乡、扎窝,他们比我们多一两个寨子。我们两边也打。一个土官管的都一样;高阳平(按:
四五十年代当地著名土官)管的扎窝乡是「博合基」。风俗习惯、唱歌都不一样,喝酒、死了人都不一样,念的菩萨不一样。松潘是「麦子」,没有牛脑壳,只有个别地区有牛脑壳。牛部落与羊部落的根根不一样。我常骂那些人牛脑壳不像牛脑壳,羊脑壳不像羊脑壳。我们根根就是乌木树,「尔勒玛」的根根是乌木树,说汉话的根根就是北京,说民族话的就是麻窝,说藏话的就是「彻向」,有个叫麦娃。 30.
四个小组。虽然不是姓,但都有神龛上的名字,同一个根根的人...。至少一个寨子有三户,同一个弟兄传下来的。由猴子变人后,弼石的人就有了。后来的人多,汉族的、藏族的。我们弼石是中间的人;一个沟沟上,这边没有人,那边也没有人...。我们知木林乡卡谷、乌木树、位都、热里,这些是「察合基」。我们「博合基」是,大黑水来说,红崖,和红崖县、麻窝、「施过」和「木日窝」,我们是弟兄一样。还有基尔、弼石、二木林、木都、格基,这是「博合基」;这都是兄弟一样。这是分起在的;他们整我们,我们整他们的。原来土官,还有老百姓,这是分开在的。我们弟兄之间分家一样的...。「察合基」是心不好的人,人到那去用火烧、烤起;「博合基」不是这样的人。麻窝和我们这一团人,我们是一家人。「施过」和「木日窝」,贵泽跟弼石,还有一个麦札,一个贵泽,我们是一家人,弟兄一样。我们四弟兄,原来是四弟兄,茂汶来的,一个人麻窝去了,一个人贵泽去了,一个人是弼石去了,有一个人家里坐了...。人是这样出来的。
例29报告人认为同是「察合基」的寨子是「同一个根根」,也就是有共同的祖先。而且,他把同一根根的「察合基」等同于「尔勒玛」,根根是乌木树。这一方面由于他自己是乌木树人,另一方面,当年乌木树土官是这一带「察合基」中最强大的土官。尤其,他说北京是说汉话人的根根,麻窝是说民族话人的根根,更显出他认为被同一权威管辖的、说同一种话的人,是同一个根根。同时,这也显示在这位老人的概念中「尔勒玛」只是指小黑水地区「察合基」各寨的人;此与目前中年与青年一辈的人认为「尔勒玛」是指藏族或黑水人有些不同。
例30报告人的口述中,事实上提到几种不同的「弟兄关系」。首先报告人说:「虽然不是姓,但都有神龛上的名字,同一个根根的人」。这是指黑水、小黑水村寨中所谓的「家族」;以家族祖先神为代表,同一祖先神的是同一个根根。一个村寨中各户常分属于几个这样的「家族」,而这些「家族」又经常由弟兄关系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溯这种「至少一个寨子有三户」相当亲近的家族血缘时,他说这是「同一个弟兄传下来的」(而不是说传自同一父亲)。其次,他提到所有的「博合基」都是兄弟一样时,似乎只是以弟兄感情来强调彼此的亲密关系。但另外他以一个「四兄弟故事」把麻窝、弼石、麦扎一带部分的(或全部的)「博合基」联系起来;这又是指具体的弟兄关系。最后,他以「我们之间弟兄分家一样的」,来形容「博合基」与「察合基」间的敌对关系;这是弟兄关系的另一种隐喻。
虽然这报告人认为大黑水麻窝人是「博合基」,但现在知道「博合基」与「察合基」之分的麻窝人不多。甚至有些麻窝人认为当地人都是「察合基」,小黑水的人都是「博合基」,两者的根根不同。这个例子也显示,经常人们不注意别人自称什么(是不是自称尔勒玛),或信什么样的佛教(是察合基或博合基);对小黑水人的敌意可以使麻窝人忽略小黑水人也自称「尔勒玛」,并认为那的人都是敌对的「博合基」。
以上这些「弟兄故事」广泛分布在岷江上游与北川的羌族与邻近藏族村寨之中。从以上举例看来,这些「弟兄故事」有不同的结构与内涵;包含了不同的时间、空间与人群,也包含了许多的「过去事实」与「对过去的虚构」。而且,它们与一些其它形式的社会记忆——如「历史」、「传说」等——共同构成一个社会对「过去」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弟兄故事」相对于「历史」而言,在各个社会中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有些地区它仍是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记忆,「历史」毫不重要;在另一些地区,「历史」成为最真实的过去,这些弟兄故事只是少数中老年人记忆中过去的传说而已。以下我将分析这些兄弟故事中的时间、空间与相关的人群认同,以及「兄弟故事」在汉、藏文化影响下的变形与发展,藉此我们或可以了解这些地区人群认同的本质与变迁,以及「汉化」、「藏化」与「民族化」所带来的族群认同本质变化。我也将尝试由「弟兄故事」来探讨「历史」与「神话」,「史实」与「历史建构」间的关系等问题。 弟兄故事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从前一篇文章中,我曾说明凝聚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产生于族群间共同血缘想象,表现在「同胞」或「brothers
or sisters」这些仿真手足之情的族群内称呼及相关历史记忆之中(王明珂
1994:125-26)。因此,「弟兄故事」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此种历史记忆或想象。然而,为何是「几弟兄的后代」而非「一个英雄祖先的后代」——如亚伯拉罕、成吉思汗或炎黄后裔?这必需由岷江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来理解。 环境与经济生态
岷江、湔江及其支流在此切过青藏高原边缘,造成高山深谷地形。这种高山间的深谷,当地羌族以汉话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一个个的「沟」之中。河有主流、支流,上游、下游之分,因此村寨所在的沟又常有大沟、小沟、内沟、外沟与沟口之别。 森林主要由松木林构成,林子里盛产各种菌菇类植物。森林上方近山棱的缓坡,高度约在海拔
3500-4000 公尺之间,是羌族放养旄牛与马的地方;在这儿树林呈零散分布,然而由于日晒充足成为良好的草场。森林下方的半山腰,被人们辟成梯状农地,种植各种作物。村寨便在田边或中间。整个山区除林木、菌菇之外,还盛产各种药材。在过去,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近年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滥伐、滥猎,森林覆盖急速减缩,动物也少了很多。 总之,本地自然环境上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丰富资源,提供人们多元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在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使得沟中村寨居民相当孤立。羌族村寨居民便在此有相当程度封闭性的环境中,在半山上种植多种作物,在住家附近养猪,在更高的森林中采药材、菌菇与打猎,在林间隙地牧羊,并在森林上方高山草场上放养马与旄牛。每个家庭都从事多元的经济活动,因此每个家庭都是独立且有相当程度自足性的经济体。 农业是羌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老一辈的村寨农民,或高山深沟中的村寨农民,他们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生计安全与最小风险为主要考量。因此,种植多种作物最能符合此目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险,使得当季的作物可能荡然无存。然而只要有几种作物收成好,配合其它的收益,一家的生计便能得到保障。相反的,「最大利益」没有多大的意义。[7][7]
因为交通困难,多余的产物很难运出去供应市场。再者,在村寨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所谓「富有」只不过是柴火、粮食与猪膘储积多一些。然而像这样的家庭,村民们也期望他们慷慨。对别人慷慨也是一种「避免风险」的农村道德;对亲友慷慨,在有急需时也能得到亲友的支助。在此采传统农业及多元化经济策略的村寨中,贫富常常只是家庭发展阶段与成员多寡的反映。主要原因是,除了获利不多的农业外,这儿有多元的资源;关键在于一个家庭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获得它们。一个年轻的家庭――如男女主人带着一两个尚年幼的孩子――由于人手不足常是最穷困的家庭。相对的,如果子女都成年了,而家长又有能力将已婚的儿子、媳妇与女婿系在家庭内,掌握这些人力的分工与运用,则便是较富有的家庭。然而,这样的延伸家庭通常无法维持长久,在一段时间后便分成一个个的小家庭。而且弟兄愈多,家庭财富愈分散,因此家庭财产不易累积。就这样,一个寨子里的各个家庭在经济上得维持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来说,在1949之前,除经营鸦片生意的土官家族较为富有之外,村寨中的贫富之分只是家庭的发展阶段与个人的能力不同而已。 在这样一个个受地理环境切割的小区域之中,每一区域在生计上都成为一个基本上可自给自足的单位。因此,除了家庭有自己的田地外,每一家族、寨、村、沟中人群都分享、保护共同的草场与林场范围。通常各村寨彼此尊重各自的地盘,但在交界之处或大山顶上,经常发生因放牧、采药或打猎引起的村寨间冲突。当地一句俗谚,「山分梁子水分亲」,说明了地理环境区分与人群区分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岷江上游的山区,最普遍的家庭结构便是父系核心家庭。几乎毫无例外,结婚后的儿子立即,或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家屋与独立的家庭。一个儿子(通常是最小的)继承老家与父亲最后遗留的产业。本家族或本寨土地不足以建立一个新家庭时,男子便经常到邻近村寨或沟中缺乏男性劳力的家庭去「上门」(入赘婚)。在一个村寨中,同一父辈或祖辈弟兄分出的几个家庭,彼此记得共同的血源关系,并成为在经济上、劳力上彼此支持的群体。同时,由于土地匮乏,分产常造成弟兄间、叔侄堂弟兄间的紧张与对立。可追溯的家族记忆通常只有两代,大多数人不记得祖父的名字;只知道那几个家庭是「祖祖或父亲的弟兄分出去的」。
在较大的范围里,村寨中有同祭一个家神的「土著家族」(如例30),与同姓并宣称同一祖源的「汉姓家族」。由例23中可看出,有些汉姓家族可能是土著家族由于冠汉姓与「假借祖源记忆」而形成。无论如何,这些「家族」都常由「弟兄故事」来凝聚;他们都彼此互称「家门」,也就是所谓「同一根根的人」。同一「家族」的人不能通婚;死后葬在同一火坟。丧礼是强化这种人群聚合的经常性场合。一个寨子经常包括几个「家族」,此种「家族」借着各成员家庭对神龛上家神的崇拜来凝聚与沿续。然而我们不能由单纯的亲属关系与祖先崇拜来理解它。兄弟分家时,以分香火的方式沿续家神崇拜固然普遍,但由于家神也是家的地盘神,因此在某地盘上建屋,或迁入某地,而开始祭某家神的情形也很普遍。更重要的是,同一「家族」的人可共享或划分属于本家族的草场、林场,也共同保护此共同资源。因此,一个「家族」的人不宜多(分享共同资源的人)也不宜少(保护共同资源的人)。在此生态因素下,失忆与重构家族记忆的情形自然非常普遍。另外,一个「家族」经常包括几个不同汉姓的家族,他们间也由弟兄故事凝聚,经常这也是内部成员不许通婚的群体。在有些例子中,由于结家门的事发生在一两代前,所以报告人清楚的知道两姓或三姓是为了强大势力而结为家门;为了强化凝聚,他们也想象彼此有共同血缘而不内婚。
在更大的范围内,一个寨子,或几个寨子聚成的村子,或几个村或寨所构成的一条沟的人,也都是一层层分享、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寨子有本寨的草山、林场,村子有几个寨子共同的草山、林场;都界线分明。各寨各村的山神菩萨,与较汉化村寨中的各种庙子,也就是这些界线的维护者。一位小姓沟的年长报告人对「山神菩萨」作了以下的铨释: 31.
山界,我的土地是从那里到那里。山界界长,其它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祖祖辈辈,几千年、几万年留下来,这个不能忘;这个山坡是怎么传下来的。为什么要敬祂?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我们一组的是「学都」。大菩萨,那就是一转啰;那便就是两个组的菩萨,「学务」喇撒。保护界线里的人。有近的界线,有远的界线;有近的菩萨,有远的菩萨。
在较汉化的村寨中,只是「山神菩萨」被「庙子」取代,其在「区分」上的意义则没有差别。如黑虎沟「二给米」寨一位老人所言: 32.
二给米,三个陀陀(按:三群人之意)。我们庙子,大庙子中间有三尊神。中间是龙王;这是黑虎将军;这是土主。任、余二姓上寨是土主;中寨就是严、王二姓,分的是龙王;下寨是黑虎将军。分了的。为什么分呢?赶会的嘛。七月七土主会,六月十三龙王会,四月四日将军会。地界也这样分。这菩萨背后朝这方向是中寨的;这菩萨背后是我们的;这菩萨背后是他们的。放羊砍草都不能侵犯的。各大队各大队之间,就更不能过去。
在祭庙子或山神(喇萨)时,每一家庭都是对等的单位,都需派代表参加。在许多地方传统习俗是,「点名」时每一家若有人参与,就在木头上作一刻记。在寨子间的共同仪式中,虽然寨子大小有别,每一寨子也是平等的。
如前所言,由于在经济上沟的独立性,以及在自然环境上沟的封闭性,使得「沟」成为值得共同保护的重要资源,「沟中的人」因此成为相当孤立的人群认同单位。其次,各沟各寨人群的生计方式类似,使得他们彼此竞争中间地区的草场、林场等资源。再者,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流行种植鸦片,因而造成武装地方豪强、外来军阀部队与盗匪横行。这些因素都造成村寨或沟的孤立与封闭,以及对「外来人」的敌意。[8][8]
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我们才能理解过去岷江上游村寨人群认同的最大范畴——「尔玛」[9][9]
在人群认同与区分上的意义。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明,茂县黑水河流域的羌族中有「赤部」、「而」与「尔玛」的人群区分概念(王明珂
1997: 333)。「尔玛」是指「我们的人」或本族的人;「赤部」是上游的野蛮人,或说是吃生肉的人;「而」是下游狡滑的汉人。现在一般羌族,特别是羌族知识分子,都将「尔玛」(以汉文书写与发音)等同于「羌族」。但中老年人却还记得,从前他们都以为「尔玛」就只是本沟或本地区的人(如例34);他们将所有上游的人都认为是「赤部」,将下游的人群视为「而」。因此自称「尔玛」,并称下游沙坝人为「而」、上游曲谷人为「赤部」的三龙人,在沙坝人眼中则是「赤部」,在曲谷人眼中则是「而」。 在黑水河上游地区,则如前文所言,各地的「尔勒玛」都认为上游各村寨人群是「日基部」而下游村寨人群都是「日疏部」。在茂县东路的水磨沟与永和沟等地,则各地区的人都自称「玛」,而称下游各村寨人群为「而」,西路与北路的各村寨人群则是「费儿」。在北川的白草河与青片河流域,在1949之前,城镇的人骂山村的人「猼猡子」或「蛮子」,山间各下游村寨的人骂上游的人「猼猡子」或「蛮子」,而各地的人都自称汉人。如此,当地一句俗语「过去一截骂一截」,便是以上「尔玛」认同(茂县、黑水地区)或汉与非汉关系(北川地区)的最佳写照,也说明过去这一带人群认同的孤立与封闭性。
目前,孤立与封闭的区域人群认同并非是绝对的。在同一寨子中,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背景、社会活动范围的人,对于「尔玛」的范围都可能有不同的认知。也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弟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流传着。而且,在这样的认同体系中,「赤部」与「而」并非是完全不能交往沟通的人群。在迫不得已时,他们(男人)可以到邻近「而」的沟或地区去上门,或由「赤部」的地方娶妻。这些由外地来的家庭成员,成为本寨的一份子。 村寨社会中的弟兄关系
由以上村寨的地理与人类生态背景,家庭与社会结构,村寨人群的认同以及与外界人群的关系,我们可以探讨「弟兄关系」在当地社会中的种种隐喻,及这些隐喻在各种社会行为上的表现。这些隐喻有些是当地特有的,有些反映许多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
首先,弟兄关系表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也就是藉此强调「同胞」人群间的根基性情感。在村寨现实生活中,关系最密切的便是有弟兄关系的两、三个家庭;往来频繁,平日相扶持。若非如此,在村寨中便成为大家谈论批评的对象。在有些地区,村寨中还流行结「异姓家门」。两个或三个家族结为一体,在婚丧习俗上遵循同一个家族内应遵循的原则。在采访中,我常听村寨民众说起异姓家门:「我们感情像弟兄一样」。结异姓家门的理由,民众非常清楚――为了壮大寨子,大家团结免受人欺侮。因此他们也很清楚,这是不同根根的人群。更普遍的例子是,几个异姓兄弟到此地来发展成几个家族的说法;在这样的例子中,他们认为这些「异姓」事实上就是同一根根的「家门」。即使与最不可能有亲缘关系的「汉人」与「蛮子」间,「打老根」也是此种弟兄关系的延伸。借着村寨中某一人与「汉人」与「蛮子」的私人结拜弟兄关系,整个寨子的人需要与「汉人」与「蛮子」打交道时至少不会吃亏。如此,在这个充满变量的边缘环境中,「老根」此种弟兄关系成为跨族群合作与避免风险的社会机制之一。 其次,弟兄关系也显示人与人间、人群与人群间的区分。弟兄们结婚后分家,在当地是普遍的家庭发展原则。在上引所有故事中,几弟兄都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落户;这是当前各人群区分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以弟兄故事记忆相联系的几个家族或寨子,也以某一弟兄的后代来彼此划分。此种区分还经常以一些物质或文化符号来强化;如例17中杨姓弟兄中有「下堂的」、「没有下堂的」;例10与例25中几个寨子划分谁是「分得牛脑壳的弟兄后代」,谁是「分得牛尾巴的弟兄的后代」;例16,分到铁甲的与分到铁盔的等等。此种合作中又有区分的人际关系,与当地经济生态中的资源分配与分享相契合。
第三,在区分之中弟兄关系也隐含人与人间、人群与人群间的敌对关系。这种弟兄间的敌对关系,在世界各文化中相当普遍。研究神话与圣经的学者,曾指出圣经中几组敌对的弟兄――Cain
与
Abel,Jacob
与
Esau――并铨释其隐喻(Girard
1977: 61-63)。在中国神话或古史传说中也不乏这类的例子,如舜与象,黄帝与炎帝。羌族民间也流传一些坏哥哥如何在分家后欺侮弟弟的故事。虽然报告人大多强调自家弟兄间的情感如何好,但他们也常闲话他人或前人一些弟兄阋墙的事。如以下永和报告人的口述: 33.
(永和甘木若)我们白家就这样分开;四弟兄,老大那里呀,老二又那里呀,老三又到那,幺弟兄又到那,都是这样说的。这四弟兄原来都是一家人,他们的子孙分开来……。四弟兄那时是很强的,后来就落败了。白家祖先留下的只有一家子。四弟兄分家不平,拿刀砍中柱子。 由于分家后的弟兄经常有些纠纷,因此敌对的「弟兄」隐喻常被用在更大范围的敌对人群关系上。如例30报告人所言:「他们整我们,我们整他们的……我们弟兄之间分家一样的。」;或如例11,报告人便直认为当前以黑水河为界区分为「掐合部」、「瓦合部」的人群是敌对的两弟兄的后代。
为何「同一根根」平时又有密切往来的「弟兄」,在当地(以及世界其它文化中)经常暗示着人与人间、人群与人群间的敌对情绪与行为?Rene
Girard 以相互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与异类替身(monstrous
double)等心理因素,来解释此种以敌对弟兄关系为隐喻的人类社会中敌意与暴力的根源(Girard
1977: 143-68)。此欲望在他的解释中不一定是真的需要,而是因为一方需要所以另一方就模仿对方的需要;在模仿中,对方成为自己的异类替身。对羌族地区的「弟兄」而言,相同的欲望却是相当现实:他们都期望能从父亲那分得土地、房屋以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在此资源匮乏地区,分家后弟兄们分得的田业总是不足,或总有几个弟兄要另谋出路;或到别的家族或寨子去「上门」,或到外地开荒、打工。因此分家分产当时造成的争端,或过后个人的失败与挫折,都容易造成弟兄间的敌意。此种「弟兄」间的敌意,也经常见于宣称有弟兄关系的邻近村寨间。为了争草场、林场,或在祭山会或庙会中各自夸耀势力,或为了婚姻纠纷,邻近村寨间常存在普遍的紧张与敌对关系。 最后,「弟兄关系」也暗示前述有区分、合作与敌对关系的个人或人群,是一个个对等或平等的单位。在一寨子中,组成寨子的是一个个弟兄分家后建立的家庭。在祭山、祭庙子或丧葬仪式中,无大房小房之分每一家庭都必须有代表参加。在更大范围的人群关系上也如此。邻近寨子间有竞争、夸耀,各个寨子有大有小,然而在相互关系上却是对等的。虽然大寨子可能欺侮邻近弱小的寨子,但即使在五十年代以前,也没有一个寨子能掌握或统治另一个寨子。因此报告人说「我们像弟兄一样」或「我们像弟兄分家一样」时,无论指的是人群间的团结或敌对,都表示各人群单位间的对等关系。这种平等或对等特质也表现在村寨中一种共同议事的传统上。寨中或几个寨子间,常有一片被称作「议事坪」的小块平地。据称在过去,村寨大事常由各寨中各家庭、家族代表在此共商解决。 在以上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弟兄故事」作为一种「历史」的特殊生态与社会意义。这些「弟兄故事」是一种「历史记忆」;以弟兄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经济社会关系上对等的、在生计上既合作且竞争的人群。现实生活中弟兄之间的手足之情,被延伸为寨与寨、村与村人群之间的情感与合作关系。同时现实生活中,分家后弟兄们各自建立的家庭的独立性与彼此的对立竞争,也投射在由「弟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寨与寨、沟与沟人群间的紧张敌对关系上。寨、村与沟间人群单位的独立平等(egalitarian)特质,以及他们之间层化的合作与对立关系(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cooperation),与当地社会强调「几弟兄」的记忆(而非一个祖先记忆)是一致的。 弟兄故事中的时、地、人、事、物
作为一种凝聚社会认同的历史,「弟兄故事」与我们所熟悉的「英雄圣王祖先」历史有相当的差别,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社会环境与政治结构下的特殊历史心性。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在历史述事中它们都以一些时间、空间、事件、物品与人物等文化符号来使之产生意义。 所谓「英雄圣王祖先」历史,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典范历史的起始部分;中华民族之国族建构中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史」,或是以「国父」或开国元勋之功业为起始的各国历史,都是此种历史的反映。所有这些历史中,时、地、人、事、物共同组织成一种社会记忆,以共同的「起源」强化某人群的凝聚及表现此人群之特质。以中国民族史为例,其源起之人物为黄帝、炎帝等等,其时为五千年前一线绵延而下,其地理空间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往外延伸,其事为涿鹿之战与许多创造发明,其物为衣裳、五谷等等,其组合则是以衣冠食谷为自我文化特征的中国人之共同起源。在历史述事中,弟兄故事也包含了空间、时间与时空中的人、事与物等因素。然而由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知,弟兄故事与典范历史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述事方式。 时间
此处所讨论的是历史时间的问题。所谓历史时间,是相对于个人的生命时间(从幼至老的成长)与自然时间(一日一年循环)之外的一种社会时间概念——表现在大都超乎个人经验的社会人群与宇宙世界的起始、发展与沿续之上。由这些弟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当地有三种「历史时间」概念。它们经常是并存的——它们并存在一个村寨中,或并存在一个报告人的记忆中。同一报告人可能说出包含三种历史时间的不同故事,而它们之间并没有矛盾;这也反映了当地「中国少数民族」认同的驳杂性质。
首先,有些人讲述这些弟兄故事时,他们心目中的时间概念非线性亦非循环,而是一种由一模糊的「过去」与较清析的「近现代」组成的历史时间概念。「几个弟兄到这儿来然后分家」的故事,或不只一个此类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如例
9, 10, 11, 13)。如此,「弟兄故事」凝聚当前村寨人群的认同;几个不同的弟兄故事凝聚不同范畴的人群认同。在这样的故事中,「过去」造就「现在」,「过去」铨释「现在」。另外,在本文中我未举例但更普遍的「弟兄故事」,则是他们的父祖与其兄弟分家的故事。羌族村寨民众的家族记忆通常很浅,[10][10]
有汉姓的家族通常也只能追溯到祖辈弟兄亲属,再远就是年代不详的「几弟兄来此分家」记忆。在更深山里的村寨中,有时人们只能追溯到父亲那一代。如此,弟兄故事在「时间」上可以归类为两群:一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一发生在「父祖那一辈的过去」。在同时记忆这两种弟兄故事的民众心中,历史时间并非是线性沿续的;发生在遥远过去的弟兄分家事件,与近现代父祖兄弟分家事件之间,有一大段的时间缺环。历史时间也非两个或数个弟兄分家事件的先后重复或循环;几个发生在遥远过去的弟兄分家事件,其时间先后经常不清楚。如此,历史时间由两个阶段构成:一是模糊的、无可计量的「过去」;一是可计量的、一代或两代前的「过去」。许多深山村寨老年人或妇女记忆中的「弟兄故事」,多属于这种只有模糊的过去与清晰当代联结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时间类型。
第二类型弟兄故事可以当做是第一类型下的变异,其普遍模式是:「几个弟兄分散到一个大范围的地区,然后其中一人的后代几弟兄到这儿来」(如例22)。或是,几个发生时间有先后的弟兄故事,表述不同层次社会人群的共同来源(如例15)。此种发生在由远而近的历史中的弟兄故事,凝聚由疏而亲的不同范畴人群认同。在这样的模式中,历史时间只有相对的先后,这是一种「相对性的历史时间」,或历史时间呈现在数个弟兄分家事件的循环之中。
第三类型的历史时间便是线性的历史时间。在大部分早已接触汉文化的村寨民众记忆中,特别是在有汉姓的家族群众记忆之中,兄弟故事被置于线性的历史时间架构里。那是,「湖广填四川的时代」,「过去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在何卿平番乱的时代」,明代或清代。这个「历史时间」与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结合在一起。这通常不是紧密的结合;由汉人观点看来,历史时间经常有倒置、错乱。简单的说,是不是完全紧密的平行结合,在于口述报告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知识,以及他如何选择一些有意义的「过去」来铨释「现在」。这样的弟兄故事,一方面解释并强化当前本寨、本沟或本家族的人群认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与无法回头的历史;那一个起点——「湖广填四川」、「过去在青海被打散」、「何卿平番乱」——也解释了作为「住在山上的人」或少数民族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
可以说,在有关「中国历史」记忆广泛而普遍的深入岷江上游山区村寨人群间之前,第一类型与第二类型「兄弟故事」可能是最流行、最普遍的社会记忆。因为这与土著语言中「时间」与「过去」的概念相契合。在本土语言中,有相当多的词汇被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生命时间,以及一日、一年的自然循环与人的作息时间。但超出个人生命及家族生命(两代或三代)之外,时间(所谓的历史时间)概念便非常模糊,词汇也变得贫乏。一个词
gaitanpu 形容很早的时候
[11][11],大致可译作「过去」。如果要强调更早的时候,则是
gaitanpu gaitanpu,「过去的过去」。在记忆所及的「过去」,他们以羌语说「红军过境的时代」(1935)与「涨大水的时代」(1933),也就是泛指三十年代或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在此之前的时间似乎都是
gaitanpu。红军过境与涨大水的时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是自身记忆所及或父祖辈口述中的「过去」。gaitanpu
时期所发生的事,则是一些介于虚幻与真实间的事(包括所有的神话传说),以及过去结构性重复发生的事(如弟兄分家、村寨间的战争、动物吃人等等)。因此,以
gaitanpu 来表达的历史时间是「同质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时间」;或者
gaitanpu gaitanpu 可以表达第二类型「相对的历史时间」。如果要表达「绝对的线性历史时间」,那么只有使用汉语及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概念了。 地理空间
在空间上,这些「弟兄」所来自的地方有近有远,还有一些只是来自含混不明的外地。这些弟兄来到后所分居的地方也有狭有广,还有一些去向不明。基本上,所有弟兄故事都说人是外地来的。这些外地,最常听到的在阿坝州有茂汶、阳柳沟、松潘(包含草地与黑水)等;在州外的四川省有崇庆、安岳、灌县等;较广泛的地区则有湖广(湖北麻城孝感)、甘肃、青海、四川、黄河流域等等。每一地名结合与之有关的历史记忆,都代表一种空间上的起源认同。譬如,黄河流域代表「炎帝后代」的起源;青海或甘肃经常与「历史上西北一个强大、好战的羌族」等记忆联系在一起;湖广或四川、灌县、崇庆,代表本家族的汉人或四川人根源;草地或黑水,代表与粗犷勇武的藏族共同的起源。有些弟兄故事中并没有提及这些兄弟是从那儿迁到本地来的。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兄弟出现在本地就是一个「起源」;另一方面,「不确定的来源」可以成为该人群在认同上的一个开放的起源。
在弟兄故事中,诸弟兄分别落居的空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弟兄们到一地分家后,分别建立几个寨子,他们因此成为当前往来紧密的几个寨子的祖先。在此,弟兄故事与当前村寨空间人群的认同与区分是一致的(如例10,
13)。讲述这一类故事的典型地区是小姓沟埃期村。三个寨子的民众,便是过去三个弟兄的后代。彼此虽有竞争对立,但三个寨子是平等的。我群全在一寨或一村的限定空间中。故事中也很少汉人的地理与历史概念。 第二种情况是在另一些弟兄故事中,特别是在有汉姓的家族故事中。这些弟兄后裔们的空间分布是跨越村寨的;他们只是一个寨中的部分家庭,还有一些家庭可能在邻近寨中或更远的地区(如例1,
17, 18, 23, 24)。这一类故事可以理县、北川等较「汉化」地区的为代表。在这些弟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区分谁是先来者、谁是后来者,以及跨村寨的血缘关系或血缘想象所造成的社会阶序。我群(汉姓家族)可能分散在其它村寨空间之中。此类弟兄故事中也有较多的汉人历史记忆与地理概念。 第三种情况是,几个兄弟分别落居于相距甚远、少有往来的地区;他们落居于不同地区的后代,目前在日常生活中也少有接触(如例3,
8, 15, 20-22)。这一类故事多出于与外界接触广的人或知识分子的口述;文献(族谱与历史著作)是重要的记忆媒介。此类故事,地理空间想象中夹杂更多的汉人历史与地理知识,而在此空间想象中不只包括有共同认同的「我群」,还包括期望中的遥远、广大空间中的「我群」想象。以上「弟兄故事」中弟兄所落居的三种不同空间变化,似乎显示当地社会复杂化程度,或对外接触程度之不同。
时空中的人、事与物
除了时间、空间因素之外,这些故事中还有主轴之「人/弟兄」,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作为插曲的「事」与「物」。首先,故事中的人,一些弟兄,隐含三种并存的社会意义:(1)这些弟兄的后代,或同一弟兄的后代,来自同一根根(血缘),因此是不能相互结亲的群体;(2)因来自同一祖先或有弟兄关系的祖先们,所以大家应和谐、合作;(3)祖先源自不同的弟兄,也使得村寨人群间有区分、竞争与对立。所有这些故事中的「事」与「物」,主要的功能便是「记忆的强化或提醒媒介」,以辅助表达以上三种故事中的弟兄关系隐喻。
故事中的「事」与「物」相关联——「事」强化弟兄故事的戏剧与趣味性;当前可见的「物」则提醒或修饰这些记忆。譬如,在例10中:「金个基那个梁梁」、「老鸦」是「物」;「过了梁子小孩学老鸦叫就会说话了」是趣味性的「事」。两者结合强化一个「弟兄们」迁徙的记忆,并以那个山梁作为「较美好的当前状态」的起点。提醒过去共同起源的现实存在之「物」,最常见的是故事中这些弟兄刚到来时的落脚点。如例14,几个弟兄刚来时「坐在月眉子那个墩墩上」;例4、5中的「三棵树」。土墩、三棵树这个现实存在物,帮助记忆一些重要的起始事件。这些「共同起源」凝聚村寨人群,并在某种程度上划分可结亲与不可结亲的人群范围。
这些弟兄故事中的事与物,也被用来强调几个寨子间的区分与优劣;此亦表现亲近寨子或家族间的竞争与对立。如例16中,几弟兄分别得到铁盔、铁甲与银人;又如例10与例25,几弟兄各自分到牛脑壳、牛尾巴或牛皮子;例21与24中,三弟兄的后代各自以「面堆起的尖尖」、「老鸦飞得的地方」来形容本地的美好;在例13中,阴山面的两个寨子以「大哥是跛子所以占居较好的阳山面」,来合理化该地目前的资源分配关系。在所有以上例子中,「物」以及相关的「事」不只是作为人群区隔的象征,也是人们主观上划分人群优劣高下的符号。人们经常以这些故事互相争辩、讥讽。然而在此重口述记忆传统的社会,相对于主要以文字记忆区分彼此的人群社会而言,这种历史述事较难以典范化、权威化而成为社会阶序化的工具。 弟兄故事中的历史心性及其变迁:汉化、藏化与民族化
为何是「弟兄故事」,而非其它的「历史」,凝聚这些山区的人群认同?关于此问题,我们的探讨必然超越「历史事实」与「历史述事」[12][12]
而涉及「历史心性」的问题。在本文中,「历史心性」的定义接近西方学者所谓的
historicity 与
historical mentality。它指的是流行于群体中的,个人与群体存在于历史时间中的一种心理自觉。它产生于特定的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透过历史心性,一群人以其特有的方式集体想象什么是重要的过去(历史建构);透过历史心性及历史建构,一群人集体实践或缔造对其而言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创造历史事实);历史心性下的历史建构与历史事实,强化或改变各种人群认同与区分(同时或也造成历史心性的改变),藉此一群人得以适应当地生态与社会环境及其变迁。 从上节弟兄故事中时、地、人、事、物之分析,我们可看出其与典范历史述事间的差异;这也反映了不同历史心性下的差异。如果我们以小姓埃期沟中所流传的兄弟故事,与我们所熟悉的典范「中国历史」相比较,更能突显此种「历史心性」的特点。首先,在他们心目中一个人群的「历史」始于「几个弟兄」,而非一个「英雄祖先」(如黄帝)。其次,「历史」中的人、事、地、物等内涵非常简单;没有帝王、英雄、圣人等特定人物,也没有战争、暴政与叛乱等事件。第三,在此种「历史」中,历史时间只由「遥远的过去」与「近现代」构成,「遥远的过去」是没有质量的时间——没有比较好的或比较坏的时代,也没有可计量的年代;没有线性的历史时间(朝代更迭),也没有连续循环的历史时间(治乱替生)。第四,此种「历史」主要赖口述来传递,而非靠大量史籍档案来保存与传承。第五,以此历史记忆所强化的是小范围的、内部较平等的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而非广土众民、内部阶序化的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
这样的历史心性由当地特殊的生态与社会环境所造成,它也维系当地特殊的人类生态与社会环境。故事本身的「弟兄关系」,呈现并强化邻近社会人群(寨、村与沟中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在一条沟中,这样的几个村寨人群各自划分沟中的资源,也共同保护沟中的资源。除了女性成为边缘弱势者之外,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社会;任何的社会阶序化与权力集中化都是不必要或是有害的。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如某些寨子灭绝,或新的寨子由老寨子分出来,在此种历史心性下「过去」很容易被遗忘,而原来的弟兄故事被修正,当前几个寨子又是传自于几个同时到来的弟兄,以维持寨与寨间的凝聚与对等关系。相反的,在如「中国人」这样有长远文字历史传统的人群中,「一个英雄祖先」常被用来凝聚一个权力中央化的人群,或强调此人群中核心群体的优越性;烦杂的英雄史迹与治乱侵伐组成的线性历史,则用来阶序化群体内各次人群,或分别谁是先来者、谁是外来的人。
「口耳相传」是此历史心性下的主要社会记忆传递方式。在同一社会人群中经常口传着不同版本的弟兄故事;不同版本述说范畴不同的人群认同。由社会记忆观点,虽然文字历史记忆同样常有失忆与虚构,然而它们与口述历史记忆仍有相当差别。口述由于不需特殊文字书写知识,因此它是普遍的;由于普遍所以不易被权力掌控或典范化,因此它常是多元的。由于它是多元的、普遍的,因此它更容易使「现在」不断的被新的弟兄故事合理化。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媒介是当地特殊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最能够维护与调节当地传统的人群认同与资源分配、分享体系。
埃期沟羌族并不代表典型的羌族。正如我不相信典范历史为唯一的历史,我也不认为有典范的羌族文化或历史记忆。埃期沟的特色是当地远离公路线,村寨居民大多无汉姓。更重要的是,当地森林尚未遭到砍伐,因而可相当程度维持村寨的经济与社会特质。无论如何,包括埃期沟在内所有岷江上游地区村寨人群,都或多或少的受汉、藏文化影响。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由于国家教育与知识宣导普及,更由于民族识别造成的新认同体系,他们所传述的弟兄故事中或多或少加入了中国历史、地理与行政空间概念。村寨人群认同中介入了其它的社会群体认同,如同姓家族(汉姓)、同县的人、同区的人,以及羌族人认同等等。每一种认同,都在线性历史中得到证实与强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许多羌族与邻近藏族地区而言,这些弟兄故事是一些在逐渐变迁或消失中的社会记忆。取而代之的或与之搀杂的,是汉人的历史记忆与对藏传佛教菩萨的记忆。因此,是否「汉化」或「藏化」改变了当地人群以「弟兄故事」为代表的历史心性,也改变了当地的认同体系?
由某种角度看来,的确如此。在汉文化的影响方面,事实上,对羌族群众来说,目前最普遍的民族起源记忆是:「羌族从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在青海、甘肃被打败后南迁到这山里来…。」这是中国历史记忆中汉晋时期「羌乱」的本地修正版。在城镇羌族知识分子中,又流传着炎帝子孙、大禹后裔或李冰、孟获与樊梨花的族人等记忆,以及相关的中国古代羌人历史(王明珂1997)。即使在弟兄故事中,我们也见到许多汉人的地理与历史概念,以及一些宣称来自汉人地区的同姓或异姓「弟兄」。中国历史记忆与家族概念,以及传播、保存它们的媒介,中国文字,无疑对岷江上游人群间的弟兄故事与人群认同有很深的影响。在埃期的弟兄故事(例12、13)中,这些弟兄没有汉姓;弟兄们的后裔正包括当前几个寨子所有的人;故事中很少汉人的历史时间与地理概念。但是,在其它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部分弟兄故事中便添增了「同姓」的人群分类因素,以及汉人的历史与地理概念。于是,弟兄故事所凝聚的人群不再是同一生态空间下所有的人,而是部分的人;或将本地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或空间联系在一起。如此造成村寨居民在「弟兄」认同上的内在分化与对外扩张化。而内在分化与对外扩张化,可说是包括中国在内许多文字文明历史心性的特征。[13][13]
因此,弟兄故事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历史心性下的线性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心性下,一方面在线性历史长流中,一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如羌族在西北被打败南迁、明代何卿平羌乱,成为造成今日羌族处境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英雄圣王祖先如炎帝、大禹、李冰、樊梨花与阿爸白茍等等取代了「弟兄」,成为定义、凝聚与区别羌族的历史记忆。
在藏文化的影响方面。黑水东部各沟村寨人群目前在民族分类上是藏族;他们说的是语言学分类中的「羌语」,但信仰藏传佛教。在这儿,弟兄故事较少。无论是村寨民众与镇上的知识分子,也几乎都说不出当地藏族或
「尔勒玛」的历史来源。黑水人认同中有一个重要社会记忆,那就是当地宗教信仰中欧塔基、欧塔咪、欧塔拉三座本地神山,各自代表在藏传佛教菩萨系统中的三个菩萨。当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她(他)们是一对夫妻与一个女儿,或是三个姊妹。没有人认为她(他)们是那些人的祖先――因为这是三个菩萨。但是在较深远的沟中,有些报告人则说这是三个同胞(不确定是弟兄或姐妹)分家产,后来分别管理三个沟。另一个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地区则是理县东部各村寨。在这儿流传白哈哈、白西西、白郎郎三弟兄的故事(例19)。同样的,在这故事与相关地方信仰中,这三弟兄也被当地羌族认为是菩萨,他们不被认为是任何人的祖先。同样的,弟兄故事在这一带比较不盛行。
为何在藏传佛教流行或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地区,「弟兄故事」或任何形式的起源历史都相当被忽视?在人群聚合上,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其实践取代了弟兄故事或线性历史,使得这儿的人们几乎成了没有「历史」的人群?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只能以田野所见的一些现象来作解释。在当地,我注意到许多宗教与婚丧仪式中,特别是在更普遍的以酒招待客人的开坛仪式中,年者要先以酒请菩萨、敬菩萨。以黑水地区为例,从最高的菩萨念起,一级级的念到包括红原、阿坝草地与黑水所有牧民与农人的共同菩萨,然后是黑水人自己的欧塔基、欧塔咪、欧塔拉,然后是各沟各寨的菩萨,然后是自家的家神。或许是对这种大小层级菩萨的信仰,以及定期与不定期的集体回忆活动(如祭本寨的菩萨或欧塔拉等),以足使重要社会记忆不断被提醒以凝聚不同层级的社会人群认同,也因此使得弟兄故事与其它形式的历史被淡化或遗忘,或被「菩萨化」了。[14][14]
由另一种角度来说,岷江上游各村寨人群中的「弟兄故事」与相关人群认同受到汉文化或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不应被简单的描述为「藏化」或是「汉化」。这样的说法预设了这儿原来就存在着汉、藏与羌三个可截然划分的「民族」。在前面我们曾说过,当地从前许多村寨人群中的「赤部」、「而」与「尔玛」的概念,表现一种相对的人群认同概念;每一条沟或地区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是「尔玛」,上游与下游人群分别是「赤部」与「而」。这与目前他们将「赤部」当作「藏族」,「而」当作汉族,「尔玛」当作羌族,且在国家宣导的民族知识下将汉、藏、羌截然划分,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我们可以说,在这青藏高原的边缘,在这华夏边缘,原来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界限,或「尔玛」与「赤部」、「而」的界线,就是一片模糊地带。中国历代王朝,北方游牧部落,西藏内地往东北扩展的政权,都曾经控制这一带地方,留下或多或少的政治、宗教与文化遗痕。但这里各沟、村、寨内外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得这些历史过程在当地社会记忆中几乎毫无痕迹可寻。直到近代弟兄故事仍是当地最重要的起源记忆,孤立的、相对的「尔玛」仍是最重要的人群认同。
因此,更重要的改变不是「汉化」或「藏化」而是「民族化」。清末民初时期,由欧美传入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在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下逐渐在此发酵、播散,而使得传统华夏与其四裔共同形成「中华民族」。「民族」(nation)概念不仅使「汉人」变为「汉民族」,也使得传统汉人概念中的「四裔」变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15][15]
为了国家民族政策的施行,民族分类与识别使得每一个人都得其民族身分,民族界限也因此被划分出来。如此使得散布于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等地的羌族范围确立。羌族知识分子学习与诠释汉人历史中的羌族史,因此建立其羌族认同(Wang
1998)。与此相关的历史是一种源于祖先英雄的线性历史。在此历史中,羌族是炎帝、大禹、樊梨花或「阿爸白茍」等英雄的后代。这种出于「一位英雄祖先」的祖源历史记忆,与「几个弟兄」的历史记忆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心性;也说明了作为「民族」的羌族与过去的「尔玛」之间的差别。
但这并不是说,「羌族」与「尔玛」没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羌族人多自称他们是「尔玛」;汉字书写与发音的「尔玛」,可以让他们忽略这个「族群自称」在各沟各寨母语发音上的差异,以及过去彼此间的认同差异。弟兄故事所表现的传统历史心性,出现在羌族知识分子所编写的「阿爸白茍」传说之中(罗世泽
1983)。一个从前流传在部分地区的神话传说人物「阿爸白茍」,被普及化成为羌族的祖先英雄(见例8,
20)。此社会记忆借着各种以汉文字出版的羌族民间故事与羌族史等传播。这看来似乎是受到英雄圣王历史的影响。无论如何,「弟兄故事」的结构仍存在,只是在新的知识体系下得到新的铨释:阿爸白茍的「九个儿子」,分别落居于他们民族分类知识中当前羌族分布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绵箎,以及历史知识中他们认为「从前应是」羌族地区的灌县、娘子关(映秀),以及语言分类知识中他们认为其居民「现在应是」羌族的黑水(罗世泽
1983)。这样的神话或历史建构,是一个混合「弟兄故事」、「英雄祖先」与「民族历史」等不同历史心性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不但表达了在民族主义下人们如何假借民族学、历史学与语言学知识来想象「我群」,也表达了此种民族认同想象的扩张性。 历史、神话与根基历史 最后,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些「弟兄故事」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传说?对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简单、截然的答案。然而这涉及一些更复杂、更基本的问题:究竟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历史与神话传说有何差别?是否所有的人类社会皆服膺此种知识理性?
许多历史学者皆认为,这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社会人群都有历史或历史意识——有些人群生活在宗教与神话掌控的世界之中;这类似于
Lévi-Strauss
所谓的
‘hot’
society 与
‘cold’
society 之别(Lévi-Strauss
1969)。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一些「非西方」人群或底层社会人群是没有历史的(Wolf
1982: 385);中国的汉族学者也普遍认为,相对于汉族优久的历史书写传统,部分中国少数民族没有历史与历史意识。然而,另一些学者,特别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人类学者或在非西方世界作研究的人类学者,却认为「神话」(myth)与「历史」(history)的区分是西方文化下的产物,此种区分不是在任何社会都有意义(Obeyesekere
1992: 59-60),或指出无所谓
‘hot’
society 与
‘cold’
society 之别,所有的原始社会都有其历史(Leach
1989: 44)。
在讨论此问题时,我们应把历史事实(真正发生了什么)与历史记忆与述事(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分别开来。在历史述事上,现在许多历史学者皆同意,「历史」常常是选择性的或是虚构的;研究族群现象与民族主义的学者也注意到,共同起源(一个祖先或事件)的历史想象常在某种群体认同下被选择、创造出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人类学者
Gananath Obeyesekere 所指出的,一个神话模式(myth
model)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论述形式再现,包括历史与人类学的学术著作之中(Obeyesekere
1992: 10-11)。这些在民族主义下的集体历史想象,或在特定文化中更深层的「神话模式」批上理性外衣的学术再现,是否就不能当作是「神话」而应被视为「历史」?这说明了在不同学术典范下或不同文化之下,人们对于神话与历史都有不同的定义。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神话与历史,或是司马迁所谓「其文不雅驯」者与历史,真正的差别只是人们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对所谓真实与不真实的过去的主观看法与集体想象。而且,在人们相信的真实与虚构之间,或历史与神话之间,有一模糊的中间地带。以本文的例子来说,岷江上游村寨人群间还流传一些有关天地开辟、创造人类、人神关系,以及某种动物或植物的来源等故事。相对于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而言,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在他们心目中非常的低;可以说他们的确分辨真实的过去与虚构的过去。然而「弟兄故事」便是介乎此二者的中间模糊带。世界许多文明中有关神性或英雄祖先的起源神话或历史,似乎都可以归入此类。认识此历史与神话的中间模糊带有理论上的重要性;探入此「边缘」可以让我们对神话如何影响历史建构与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如何投射在历史建构与神话建构之中,有更多的了解。
本文的弟兄故事,以及我曾在别的文章中论及的「太伯奔吴故事」,都是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事实或事件(historical
facts or events)、历史述事(historical
narratives)与神话传说间的关系。在弟兄故事中,我们是否可以追问「最早有几个弟兄到这儿来」是不是历史事实?或「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几个弟兄从湖广来」是不是历史事实?显然它们有些是事实,有些是想象,更有些是被修正、被想象的事实。对「太伯奔吴故事」的研究也说明,土著「寻找一位外来祖先或神」,与华夏「寻找到野蛮地区被尊为神或酋长的祖先」,这两种历史溯源(或历史想象)普遍存在于文化接触中势力强弱不均的两群体之间(王明珂
1997: 272-79)。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历史记忆(或神话模式),可能导致符合此结构的社会行为(或新神话建构);如几弟兄一起到外地开荒,或一位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征服蛮荒世界。而现实社会结构(一村有三个寨子,或文明核心与边缘人群关系),也可能产生同样结构下对过去的回忆(三弟兄到此分家,或来自文明核心的人曾在蛮夷地区被尊为神或王)。新的社会环境、知识与事件,产生新的社会历史记忆或新的历史心性,而社会人群在新的、旧的或混合的历史心性中,经验当代、期待未来,并重建他们各种版本的过去。因此,在本文对于「弟兄故事」的分析中,一个主题便是某种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中的「结构」——无论称之为历史结构、神话模式或历史心性,或如社会记忆研究先驱英国心理学者
F. C. Bartlett 所称的
schema(1932:
197-214)——,以及它与历史述事、历史事实间的关系。
「寻找外来的或到外地去的祖先或神」与「弟兄故事」应是根植于许多文化人群中基本的两种「历史」——介于历史与神话间的根基历史——,分别代表不同的历史心性。我称这些弟兄故事为「根基历史」,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历史事实」与「历史述事」的产生都以此为根基。另一方面,它在以父系继嗣或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人群间,以最直截的方式(弟兄关系)强调「同胞」间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而强调人群间的根基性情感,也是许多历史述事(如国史与民族史)的主要目的,以及促成历史行动与事实(如中国「同胞们」共同抗日)的主要动力。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介绍流传在岷江上游及北川地区村寨人群间的一些「弟兄故事」,并说明产生这些「弟兄故事」的当地生态与社会背景,以及故事中的人、事、物与空间、时间等概念。藉此,我强调这是一种基于特殊历史心性下的历史述事与历史记忆;我也探索这样的历史心性与历史记忆在汉、藏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化」影响下的变化。
以「弟兄故事」为代表的根基历史,最初流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彼此接触的、个人或群体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大致平等的、以父系继嗣或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群体之中(如一个小沟中各村寨人群)。[16][16]
虽然在细节上有争论,这是一个群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众历史」。随着人类社会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复杂化、中央化(centralization)与阶级化(stratification)发展,根基历史所代表的历史心性逐渐被其它历史心性取代或压抑。首先,在社会中央化之后,并非这些弟兄,而是弟兄们的父亲——一位英雄圣王——成为历史的起始。无论历史重复着一个个英雄圣王及其子孙的兴亡(循环历史),或是英雄圣王及其子孙万世一系的历史(线性历史),其「起源」都是一位英雄圣王。同时,在社会因政治、经济、宗教而分工化、阶层化之后,历史记载的不再是该群体所有人的「共同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他们是皇室、贵族、世家,或是宗教与商业领袖。政治、宗教与商业活动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取代基本历史中的「物」与「事」,成为划分、强化或争论地域、族群与社会阶层化关系的符号。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记忆活动中,文字书写取代或压抑口传记忆,扮演非常重要的记忆媒介角色。它不但被用来凝化、保存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记忆,文字书写知识与书写材料又可被垄断为一种政治资本。在社会分工与阶层化之下,某些人群被排除在这些新记忆媒介之外,因此也无法以历史记忆来争夺、维护本身合理的地位。弟兄故事中群体间的「同胞之爱」,只保存在帝王、贵戚与世家大族自身的文字历史记忆之中;所有成员(如华夏)间的一体性,转变为由异质化的边缘来强化——以历史与风俗描述来强调域外世界与域外之人的诡异与野蛮,以及对外战争中本族群的英雄人物与事迹。同时,就在此种社会文明与历史心性的发展中,一种扩张性的历史心性——寻找在边缘或蛮荒地区被土著尊为神或酋长的祖先——创造出许多华夏化(如太伯奔东吴)、民族化(如大禹在川西)或西化(如
Captain Cook 到夏威夷)[17][17]
的历史述事与历史事实。相对的,「寻找外来的祖先或神」,也在此文化接触中成为许多原以弟兄故事或其它本土历史凝聚之人群的新历史心性之一;由此产生汉化、民族化或西化的历史述事与历史事实。
以弟兄故事为代表的根基历史,似乎曾普遍存在于中国及其边缘部分区域人群间。中国古史中弟兄故事遗痕随处可见;如《国语
. 晋语》中便有黄帝、炎帝为两弟兄的说法。[18][18]
到了汉晋时期,当华夏边缘扩及于青藏高原边缘时,被纳入此边缘而成为华夏的巴蜀人,也以一「九弟兄」故事将本地人与中原华夏凝聚在一起。[19][19]
汉代之后,这些弟兄故事在历史中已失去其位置;线性或循环的历史,以英雄圣王为起始的历史,以记录、回忆社会中部分人活动为主的历史成为正史。但以「同胞血缘」凝聚人群的历史心性,仍存在于以各种方法表述的历史(特别是族谱)、传说与神话之中。最后,近代民族主义下的历史概念,如美国历史学者
Presenjit Duara 所言,强调的是一种「启蒙式」的线性历史(Enlightenment
History):一面追塑成员间共同的起源,一面强调现代与传统间的断裂(Duara
1995: 17-50)。在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建构过程中,此线性历史有一个浑沌的、介于历史与传说间的起源——炎黄。一个过去的皇统符号,黄帝,被建构为所有汉族或所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沈松侨
1998)。在稍晚的中国民族史建构中,炎帝则被影射为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所谓「氐羌系民族」——的祖先。
当中华民族由历史记忆中「觉醒」后,传统被视为四裔蛮夷的、一个个孤立的「尔玛」也变成了羌族。「尔玛」与「赤部」、「而」之间的相对关系,转变为羌、藏、汉之间绝对的民族界线。对汉族而言,更重要的是羌族在「中华民族」建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由于中国古文献曾将许多边缘人群记录为「羌」,而「羌」与中国古代之「姜」氏族又被认为是同一族群。因此姜姓炎帝不只被认为是当今羌族的祖先,也被认为是所有与古代之羌、氐羌有关之族群的共同祖先。一个古老「炎、黄弟兄故事」的新诠释,将所有「氐羌系民族」(包括藏、羌、彝、哈尼、纳西、景颇等十数种西南民族)与汉族紧密结合为中华民族下的「兄弟民族」。这说明了,虽然启蒙的线性历史以及由之产生的「民族」都被认为是近代产物;一种新的历史,新的认同。但无论如何它仍是人类以「历史」来凝聚社会人群的一种形式。也因此,在新的历史心性中仍潜藏着根基性的历史心性——在中国,「同胞」仍是民族成员间强调根基性情感的称号,「兄弟民族」仍是强调中华民族下各民族团结的符号。 参考文献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ivised 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ed. by Fredrik Barth, 9-3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h,
Marc. 1954.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Peter Putna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iade,
Mircea. 1954.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or Cosmos an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rriss,
Nancy M. 1995. “Remembering
the Future, Anticipating the Past: History, Time, and Cosmology among the
Maya of Yucatan,”
in Time: Histories and Ethnologies. Ed. by Diane Owen Hughes and
Thomas R. Trautman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irard,
René.
1977.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oody,
Jack. 1977.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bsbawm,
Eric & Terence Ranger ed.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ach,
Edmund. 1989. “Tribal
Ethnography: past, present, future,”
in History and Ethnicity, ed. by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 Malcolm Chapman, 34-47. London: Routledge. Levi-Strauss, Claude.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Obeyesekere, Gananath. 1992.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hlins, Marshall D.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5. How “Native”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Anthony D. 1987.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Stanford,
Michael. 1994.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ress. Thompson,
Richared H. 1989. Theories of Ethnicity: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Tonkin,
Elizabeth, Maryon McDonald & Malcolm Chapman. 1989.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81. The Ethnic Phenomenon. New York,
Elsevier. Wang,
Ming-ke. 1992.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1998. “From
the Qiang Barbarians to Qiang Nationality: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Bounda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in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王明珂
1994,〈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
5.3: 119-140。
1997,《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四川省编辑组
1986,《羌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李海鹰等
1985,《四川省苗族、栗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沉松侨
1998,〈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出版中。
庄学本
1941,《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印行,收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
2,民族篇
26。 政协理县文史委员会
1996,〈通化西山白空寺〉,《理县文史资料》1期(总第13期)。 华企云
1932,《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 (文章来自
:《时间、历史与记忆》黄应贵主编,
页283-34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9年4月
台北
南港)
[1][1]
在相關研究中,有的學者偏好用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一詞,有些用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或有學者予以上兩者不同的定義;事實上所討論的都是人類記憶與社會認同間的關係。無論是社會或集體記憶,它們的範疇都很廣;不只包括廣義的「過去」,也包括對現在與未來的想像與期望。本文中我以「社會歷史記憶」一方面強調此種集體記憶與某種社會認同的關聯,另一方面強調在所有社會記憶中「歷史」對於建構此種社會認同的重要性。 [2][2]
在本文中羌族知識分子是指曾受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教育,因此獲得漢文知識體系與此體系中的民族、國家與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並因此任職於各級政、黨公職與文化教育事業的羌族。 [3][3]
實際進行採訪的地區有:理縣的縣城、蒲溪溝、薛城,汶川的縣城、龍溪溝、棉篪,茂縣的縣城、永和溝、水磨溝、黑虎溝、三龍溝、赤不蘇與太平牛尾巴,松潘的縣城、小姓溝,北川的曲山鎮、治城、小壩鄉、片口鄉、青片鄉,黑水的蘆花鎮、麻窩與知木林(小黑水)。 [4][4]
由於青片上五寨位於最邊遠的支流上游,只有他們保留了一些土著原來的服飾、習俗及語言。由於這些「羌族」殘痕,以及由上游而下游各村寨的連瑣關係,許多北川羌族鄉得以被識別出來。這便是為何北川人講起本身的羌文化時常以青片上五寨為例;也因此在他們心目中青片上五寨是典型的羌族。至於茂縣、汶川則是羌族最集中的地區,建構羌族歷史文化的羌族知識分子也多出於此兩地,所以已完全漢化的北川羌族認為茂縣、汶川的人是核心的羌族。但北川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族群中心主義,表現在與汶川羌族間對於「羌族祖先大禹究竟出生在何處」的爭執之中(王明珂
1997: 350-53)。 [5][5]
在茂縣太平牛尾巴村中,有部分老人則說大爾邊、朱爾邊與小爾邊――所謂「爾邊三寨」――是由牛尾巴遷出的三弟兄所建立的。 [6][6]
許多報告人說,以前這兒雖然有語言上的不同,但並沒有所謂羌、藏區分。社會區分主要在於牛部落與羊部落之分;這是兩種不同派別的藏傳佛教。埃期的確有許多老年人是由熱務嫁過來或入贅的。村民說,在民族分類、識別之後,羌、藏區分就愈來愈清礎,通婚的也就少了。 [7][7]
八十年代以後,由於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私有制的恢復,部分村民也有了追求「最大利益」的經濟動機。近年來,花椒、蘋果、梨、李、桃、大蒜、洋蔥等經濟作物的生產,為羌族地區帶來不少財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較便利的村寨,都將日曬好的田紛紛改種經濟作物,特別是已成為當地特產的花椒與蘋果。然而,幾乎所有種花椒、蘋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種植許多糧食與蔬菜作物;沒有人成為專門生產經濟作物的農民。雖然許多年青一輩的人已不滿這種農業傳統。我聽過許多年青人抱怨他們的母親在這方面的「頑固」;怎麼說她們也不肯多撥一些田出來種市場價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溝村寨中的婦女尤是如此。 [8][8]
我們可舉例說明這種封閉與孤立的人群認同。首先,在語言上,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語言」的最大特色便是「話走不遠」。一條溝與鄰近的溝語言都有區別,有時陰山面與陽山面的村寨說話也有差別,相隔更遠一點的村寨間就不能溝通了。因此目前不同溝或地區的一般民眾均以漢話(四川方言)互相溝通。其次,羌族寨子的構築方式是石砌或木石混合的建築,一間間緊密的聯成一大片;其防衛功能是相當明顯的。較大的寨子都有碉樓或殘碉痕跡。這是一種防衛與警戒的石砌構築,經常有五、六層樓的高度。據他們說,從前寨與寨之間、溝與溝之間互相搶來搶去,打得很兇。現在許多村寨仍在相當高的山上,以及寨子的防衛性構築方式與殘存的石碉樓,都顯示他們所說的十分真實。 [9][9]
因方言不同而讀如
rma 或 ma, xma, rme 等等;由於語言的地方差異,因此「爾瑪」只是許多在發音上有或多或少差異的「自我稱號」的代號。因此,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只有自己是「爾瑪」,並非完全是在主觀上忽略別人的自稱,而是,對他們而言這些自稱的確有「差異」。相反的,當今日羌族都認為「爾瑪」就是所有的羌族時,所有這些自稱上的「差異」都被忽略了。以下若無特別說明,我以「爾瑪」代表當地羌語中「我們的人」這個詞所有的不同發音。 [10][10]
雖然在較漢化的理縣與北川等地,部分家族宣稱來此已十多代,並能述說各輩名稱排行。然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大多只記得那些人是父輩或祖輩親戚,其他的本家族人則是「家門」。 [11][11]
這是以茂縣黑虎鄉的採訪為例;在其他地區羌族中都有類似的時間概念。 [12][12]
近年來許多歐美學者,傾向於將作為過去發生的史實之歷史事件(history as event)與歷史述事(history
as narrative)分別開來。他們或以 history (e) 與
history (n), 或以
history (1) 與 history
(2) 分別二者(Stanford 1994: 1)。在本文的探討中,別於「歷史述事」的不只一些過去曾發生的「事件」還包括所有過去的「真實存在」,因此我以「歷史事實」名之。 [13][13]
這並非是說漢族或中國人好以武力擴張,而是說漢族或中國人常以歷史記憶來造成一擴張性的族群邊緣。我曾以「太伯奔吳故事」來說明華夏邊緣如何藉歷史記憶擴張(王明珂
1997)。 [14][14]
必須說明的是,這種祭拜或請菩薩的儀式活動,在茂縣、汶川等羌族地區也有。在西方的黑水或北方的松潘附近,山神菩薩被列入藏傳佛教階序化菩薩系統之中。由此往東或往南各村寨,藏傳佛教的菩薩逐漸消失,人們只祭拜各級山神菩薩與觀音、玉皇、東嶽等漢人信仰。再往東往南,在汶川、理縣等地村寨中則漢人神祇信仰取代了各級山神,各村寨最多只祭拜一個山神。在最接近黑水藏族與熱務藏族的埃期溝羌族中,則兩套系統並存;一方面他們以各種弟兄故事凝聚不同人群,同時這些人群也就是共祭各級菩薩的不同範疇人群(見例12-15的相關說明)。在祭各級山神的村寨中,似乎每一山神只代表一個或大或小的人群,而各個山神間並沒有絕對的階序。在只祭本寨山神的村寨中,過去在開罈前所請的則是平行的、鄰近各寨的山神,而非階序化的菩薩(四川省編輯組
1986: 169-170)。 [15][15]
這並不是說在
nationalism 傳入中國之前不存在「華夏」或「漢人」族群認同;然而,傳統的華夏或漢人認同,與漢民族或中華民族認同的確不盡相同。前者主要賴「異類邊緣」來凝聚(強調非我族類的異類性)。後者則是在民族主義的「民族」概念下的產物;在此概念中,漢民族或中華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緣(體質)、文化、語言等特徵並在歷史上延續的人群。本世紀以來中國許多民族學調查與民族史研究,可以說是找尋或想像體質、文化與歷史同異以建立中華民族、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特質與區分的活動。我曾以羌族為例說明此歷史過程(Wang
1998)。 [16][16]
作為根基歷史的弟兄故事目前廣泛分佈在中國西南地區以父系繼嗣或以男性為主體的各族群間。以下的例子說明,當這些西南土著被漢人分類而「民族化」之初(約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他們仍以「弟兄故事」來合理化他們心目中的民族關係。如一則有關景頗族傳說的記載,『(江心坡)土人種族甚多...。或謂彼等為蚩尤之子孫...。而年老土人則謂:「我野人與擺夷漢人同種,野人大哥,擺夷二哥,漢人老三。因父親疼惜幼子,故將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擺夷種田,供給老三。且懼大哥野人為亂,乃又令二哥擺夷住於邊界,防野人而保衛老三。後野人以山居甚苦,果然相率起魬反,打入京內。至永昌遇孔明領兵到來,受慰而返。後若干年復反,而王尚書又領兵到來,仍被安撫而無異議。今江心坡地界內肯都樣有王尚書建立的大營盤
...。」』(華企雲1932:
332)。又如,彝族(夷族)夷經中的記載:『遠古時代喬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後喬姆石奇獨活。老三喬姆石奇的三個兒子原來不會說話,他們以竹筒在火中燒出爆烈聲,三個啞巴嚇得驚呼...)大的叫
Atzige(羅語), 二的喊
Magedu(番語),小的呼「熱得很」。從此他們說三種不同的語言,成為夷(Nohsu)、番、漢三族的祖先』(庄學本
1941: 152-55)。部分苗族中亦有苗、漢、彝為三弟兄的祖先起源故事;慄僳族中也有慄僳、漢、彝為三弟兄的說法(李海鷹等
1985: 179-81)。這些例子都說明,在「弟兄故事」的歷史心性下,新的「歷史」仍以「弟兄關係」來強調各族群間的區分與對等。 [17][17]
根據許多文獻記載,歐洲探險家 Captain Cook 在 1779
年抵達夏威夷,被土著殺害然而被尊為神。基於此,人類學者
Marshall Sahlins 與 Gananath Obeyesekere 間曾有關於歷史與文化結構的綿長辯論(Sahlins
1981, 1995; Obeyesekere 1992);或請參見拙著(1997:
278-79)。 [18][18]《國語
. 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19][19]
《華陽國志
. 蜀志》: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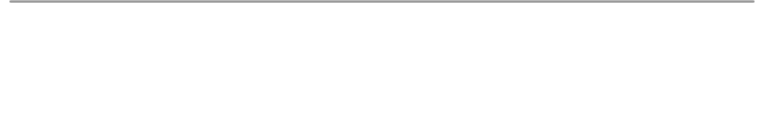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