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希光:学在长征路上 ——《讲故事的艺术——在长征路上体味清华新闻学》前言
一
到与世隔绝的高山峡谷中找故事
晚饭上,崔县长又带头唱起了藏族的《祝酒歌》:第一杯酒敬给山神,第二杯酒敬给父母,第三杯酒敬给远方来的客人……
“崔县长,你太客气了,学生们是来社会实践的,用不着这样高规格的接待。”我说。
“不,你们是北京来的尊贵的客人,十分难得,你们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客人。”他说。
“难道你们这里没有来过北京的客人?”
“自从毛主席走后,到我们这里来的最高级别的领导是罗开富老师(《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他是副部级干部。”崔县长说。
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当年毛主席带领长征的队伍到达了这片神秘的土地,黑水在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红色洗礼之后,随着长征队伍的离去,它似乎又回到了与世隔绝的状态。
2002年7月1日清晨,我带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一行20人,乘坐一辆大巴士,离开成都,踏上了黑水的征程。
黑水,这个只有月亮、雪山、激流、峡谷、原始森林的地方,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端。在古时候,人们将这个地方视为“人马为土、商旅裹足”的边寨不毛之地,英国探险家称这个地区是“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方”,即使在今天普通的中国地图上,也很难找到这个地名。但是,这里却是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人生旅途的第二故乡。
从成都到黑水300余公里,在过去骑马要走上十几天,而今天乘公共汽车,七八个小时即可到达。汽车离开成都平原后,过灌县,进入山区,我们沿岷江行进。路多在谷底,时而河阳,时而河阴。不久进入羌族人居住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羌族基本汉化,只偶尔在半山腰上看见羌族人居住的山寨和塔碉。傍晚,汽车在蒙蒙细雨中开进了位于狭长河谷中的黑水县城。
清晨,崔县长亲率6辆吉普车,冒着蒙蒙雾霭,登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垭口雪山峰顶。山顶上,晴空万里,到处开着鲜艳的野花。崔县长对同学们说:“千万不可大声喧哗,否则就可能云腾雾涌,招来暴雨,下山的路就会变得十分危险。”
同学们爬到玛呢堆上,面向藏族的神山——奥太雪山祈祷祝福。然后,崔县长带领我们步行攀登雪山,在山顶上同学们凭吊了长征时因高山缺氧和寒冷牺牲的12名红军战士墓地。
入夜,黑水县政府小宾馆的客房成了同学们的临时教室。在那里,老师跟同学们共同研究《黑水县志》,阅读各种背景资料,并与同学们共同制定人物采访框架。同学们一个一个谈他们白天采访到的故事,我挨个问他们:故事包含哪些有价值的新闻点?时效、接近、重要、后果、人文兴趣?故事最大的卖点是哪个?这个故事背后是否还埋藏着更重要故事视角?这个视角与其它故事叙述视角的比较?这个视角是否埋葬了其它更重要的视点?这个视角是否全面反映了故事或人物的整体画面?对于黑水这座历史重镇,我们更应该关注其过去发生的新闻和故事,还是正在或未来要发生的新闻和故事对黑水的影响?哪种故事有更大的新闻价值?这条故事里最值得引用的话是什么?值得写进导语里的细节在哪里?整个故事的建构可否围绕这句引语或细节展开?
我要求同学们在采访的时候,要关注这类人物的故事: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普通人的英雄事迹、各种人成功的故事、浪漫的故事。同时,要求同学们不得写个人的流水帐。
在接下来的10天里,在高山藏寨、佛教寺庙、小镇集市,同学们认真走访。他们在山村采访到了长征路上最后一位老红军战士、野外跟踪采访了每天翻山越岭的邮递员、跟踪采访了马背上的电视女记者。同学们发现了生活中大量有意义的人物和故事。从黑水回到北京一个月后,同学们分别把他们采写的故事通过电子邮件发到了我的邮箱。在阅读同学的作业时,我不断问自己:“这些文字给读者会留下了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哪些逸事、细节、引语会令读者震撼、共鸣?”“同学们发掘出来的细节,如引语、趣闻轶事等,是否揭示了长征路上这个特殊地区人物的性格、习惯、感情和思想?” 我期望,这些故事的发表,也许会使外界对黑水的人有一种新的认识和观察视角。我更期望这趟短暂的大篷车履行课堂能促使人们对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体制有一点点新的思考。
二
在真实的世界里找故事
最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中国问题观察家Philip
Cunningham和《日本时报》前主编、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岛津洋一有这样一场对话:
“《亚洲周刊》最近发表文章批评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大学脱离新闻实践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正在变成盲人摸象。”一个学生说。
“盲人摸象倒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别摸错了地方。”Philips
说。
“摸错了地方也不是大问题,关键是不要在课堂上,把摸到的屁股当成一张脸来讲解给学生。”岛津说。
这段对话听起来十分刺耳,但是,我们不妨大胆地检讨一下我们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
不久前,北京大学钱里群等教授在报纸上对中国大学教育体制进行了尖锐批判,我们的大学教育不是鼓励、保护、开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而是有意无意地伤害、压抑、以至扼杀学生的创造活力。大学培养的是学生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教育还仅仅是课堂书本上那一点点知识理论,
然后学生抄抄剪剪,按照“学术新八股”,写一些内容空洞、无创意的“学术论文”。对于这样的一种大学教育,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批评说,即便死记硬背了人类社会积累的全部知识,也不过是一台计算机,而不能算是一位“学者”。
学者是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那么新闻学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学生对新闻学核心的不理解、对新闻事业缺乏激情。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
我们的学术官僚体制喜欢以培养深厚坚实的理论功底为借口,抹煞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和职业教育的存在意义。
经过几年的新闻传播学课堂教育,学生反而写不出来故事了,对人生失去了激情,在学习、研究、写作中,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如果我们敢于公开和坦诚地拷问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在职业上和学术上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在中国新闻界的角色。
走进大学的新闻学课堂、翻开教授们撰写的专著论文,新闻媒体的总编、主编、编辑、记者、编导、制片、摄影、摄像发现新闻学术界的教学与研究与新闻界本身越来越不相干,新闻教育界传授的理论与新闻一线需要的专业知识更加不相干。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不相干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前新闻教育界的目的和动机与当前新闻媒体界相差甚远。新闻学的学者们研究和学习的动机越来越表现为满足学术官僚体制的需要,例如:申请各类课题经费的需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目的统计填表的需要;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统计数量的需要。再则,学术界和教育界学习和研究新闻学变成了满足生存者本能的需求。填表统计论文和参加越来越狭窄的学术会议变成了晋升教授的唯一指标。为了生存,研究的选题越来越狭窄。另外,学术界越来越满足于方法的完美——重形式、轻内容;重概念、轻思想。学术研究变成了追求方法上的橱窗效果和方法的技能演示。研究方法,如问卷设计,成了研究的目的。“手段中心论”取代了“问题中心论”。这造成了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这样一个结局:研究方法的完美和学术思想的贫困。
[i]为研究而研究,研究课题不是来自为了解决新闻界重大问题的热情、诱惑、需求,完全是出自一个狭小的学术领域的小圈子,仅仅为少数几个研究者的个人生存的需求,满足学术官僚体制的要求,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新闻界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一种对新闻学研究的要求和新闻学教育的态度在今天竟然在大学里变成了合法的动机。
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对新闻界和公众是一种责任,并且将得到新闻界的欢迎。但是,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新闻学?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学?好的新闻是用事实说话;好的新闻学是用研究结果说话。或者说,如果一个记者在理论上不知道“好新闻”的构成要素,他很难会写出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如果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知道何为优秀的新闻学研究成果,他也不会做出出色的新闻学研究工作。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新闻学研究?斯坦佛大学传播系主任Theodore
Glasser认为,一流的新闻学和一流的新闻学理论必须植根于于社会这个大课堂。新闻学不应该是目的不明确、无休无止的研究。
对于新闻学院的学生,最优秀的新闻作品更是出自社会大课堂。仅仅在理论上知道“好新闻”的构成,远远无法保证他或她能够采写到“好新闻”或“好故事”。正像医学院的学生,仅仅在课堂上学习了解剖学并不等于可以拿手术刀给病人开刀。哥伦比亚大学的萨伊德把新闻看作是对世界的解释。他在《报道伊斯兰》中说,新闻是一种知识形态。记者总是根据自己在其中的利益去报道世界。新闻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为存在。记者通过把自己采访的素材赋予意义和重要性,使其采写的故事娓娓动听。
[ii]
清华新闻学教育是用真实的人、真实的经历、真实的事件,讲授和感受一门关于真实的学问——新闻学。在真实的世界里寻找、发现新闻主题,发现戏剧性的故事、有人性的细节。清华新闻学是在路上学习。在过去3年里,清华新闻学的老师把课堂搬到楼兰佛教古国、内蒙古额尔济纳沙尘暴源头、太行山上、北京四合院、北京胡同、国子监、孔庙和红军长征路上。新闻学课堂大篷车满载着学生到人生的大道上采访实践。在路上,清华学生学到的是一种发现的方法、评估的方法、鉴别的方法和批评的方法。学习的是故事的叙述风格、基调和主题的选择。
去年秋天,新新闻学创始人、前《纽约时报》记者盖·塔里茨在“清华阳光传媒论坛”的报告会上对清华新闻专业的学生们说:”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清华新闻学目的是教会学生通过采访,把那些貌似单调乏味的普通人变成一个个充满了人性味的感人故事。 三
在普通人身上找故事
作为新闻学教育,最大的难题就是教学生在普通的生活中和普通人的身上寻找故事、找到新闻。这也说明新闻采访在新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把清华新闻学课堂搬到雪域高原、长征路上,目的是让同学们在实践中体验知识与理解的差别、体验理论与思想的差别。例如,新闻学的根本是教学生采集和记录新闻事实,并不加修饰地直截了当展示给受众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采访。在上个世纪,至少有3本写红军长征路上故事的著作,这3本著作都是由资深记者写的,其中由美国记者埃德家·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哈里斯.索尔茨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中国记者罗开富的重走长征路日记。在这次旅行中,我把这3本书定为每个学生路上的必读书,从中学习前辈们寻找故事的视角和采访方法。
为什么要采访?因为故事需要直接引语、需要精彩的对话。直接引语是新闻作品中最有冲击力的建筑材料。从传播效果看,是要获得鲜活的、有声有色的素材,使本来乏味的、干巴巴的信息和数字充满了人性。
记者通过在采访中提问、获得回答,然后在回答中选择记者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再把这些选择出来的信息根据新闻的写作原理组合成一篇新闻报道。记者的这种组合把一堆本来可能无太大意义的信息变成了有新闻性和可读性的故事,并引导读者根据记者的故事叙述视角和框架去关注某个事情或某个人物。
对于记者来说,在采访之前必须弄清楚应该提什么问题,或者说,记者应该尽量提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误导读者或被采访者的问题。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在新闻采访的问题设计前,记者先要弄清楚自己对新闻事件究竟知道些啥?要明白自己对事件的:知之、不知、不知不知。采访就是要解决不知和不知不知的问题。不知就是不知,千万不能带有任何猜测。
采访谁、不采访谁、优先采访谁、重点采访谁,最终都会影响你的故事叙述的视角和框架。什么人是最佳采访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是现场目击者、当事人?还是道听途说者?会讲故事的人、能说出惊人的“直接引语的人”,作为目击者,是否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被采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否能准确描述出他所观察的情况?被采访者提供的是一手信息?还是个人意见?被采访者提供的是具体的信息?还是笼统的信息?被采访者提供的信息是否核实过?被采访者是否是值得信赖的人?被采访者的叙述框架是什么?你将采用的叙述框架是什么?被采访者是否影响了你的报道角度?你的框架选择取决于你的受众还是被采访者?
有的时候,最精彩的引语发生在采访的结尾,从而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故事。如姜琳同学采访老红军长达2个小时,临结束时,问82岁的老红军:“您知道今天的国家主席是谁?”老人想了半天没有想起来。乡长给了他一颗烟点上说:“别着急,一边抽烟一边想。”老人紧蹙眉头,使劲抽烟,5分钟后,还是没有想起来谁是国家主席。“您知不知道邓小平是谁?”老人听见这话,如梦初醒,高兴地大声说道:“对了,对了,是邓小平的亲戚。” 四
谁有资格记录真实的故事?
每天早上8时,“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打破了《人民日报》9号楼的宁静,在二层的一间教室里,18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学生坐在18台破旧的打字机后面,开始了一天的课堂生活。40岁的新闻学教授、《华盛顿邮报》〉记者泰德·噶朴站在讲台上正在模拟主持一场记者招待会。
这是18年前我在研究生院学习新闻学的场景。
今天的记者和新闻学院学生不再使用英文打字机,他们坐在安静的、狭小的、打了隔断的办公区内,或坐在学校的电脑实验室里,不受任何杂音干扰地写稿或上网。
但是,无论打字机或电脑如何演变,记者需要的最基本的素质是新闻鼻和讲故事的本领。自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诞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新闻记者学习新闻学的主要方法是边干边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记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一个记者所需要的那一整套的素质和敏感是天赋的,是一种内在的能力。
记者不仅需要具备强壮的身体素质,以适应艰苦紧张的采访报道工作,记者更需要健康的心理素质。早在30年前,英国学者和记者坎德林在《自学新闻学》这本书中认为记者最珍贵的素质是要有一个善于与人相处的品性,善于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写道:“性格孤僻、惟我独尊、墨守成规、卖弄学问、举止粗俗、固执己见、教条主义、心地狭隘、盲目信仰、自命不凡、势力小人……所有这类人在新闻学的家园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iii]
从人才培养目标看,大学教育中“精英意识”的培育与新闻人才培养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记者不是矫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朴实的传播者。他们是用“普通人的声音”把事实传递给人民。
[iv]记者是与事实,而不是与观点打交道,否则记者与作家、学者、官员和政客就没有区别了。
记者比其它职业的人对社会有更大的责任。理想的法律等同于正义,医学可以拯救人的病痛。而新闻学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传播真相。新闻学是培养建筑大师,不是培养房地产推销商。建筑师考虑的是住户(公众)的利益,而推销商考虑的就是卖房赚钱。记者必须向公众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新闻或者他们有权知道的新闻。
在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伦理学是不可缺少的一门功课。在黑水,为了使同学们深层次地掌握这门功课,每天夜里,无论同学们多晚回到招待所,都要集中在一个学生狭窄的房间里,坐在床上、站在地下、坐在地下,上一堂2个小时的“夜校”。每个同学都要面对老师和全体同学准确无误地回答下面这些问题:你有足够的一手事实,能充满自信地写好这个故事吗?你所用的事实都是经过核实的吗?你报道的视角是什么?你的读者是谁?采访对象和读者对你视角选择的影响?你选取的角度是否公正?还有没有别的报道角度?你的故事报道伤害了什么人没有?你的新闻职业道德标准是什么?你是站在谁的利益和立场上写这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要坚持平衡原则。只有坚持平衡原则,才能完成社会对媒体所要求的真相与公正。哲学家Clifford
Chrisians
认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为无权无势的群体寻求公正是新闻媒体的核心任务:“一个有社会责任的记者必须是社会的镜鉴、批评者和弱势成员的辩护者。”
[v]
把新闻学课堂搬到长征路上,是为了培养一代有真才实学和胆识的记者。他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别人想不到的新闻线索和新闻故事;在新闻热点报道中,选择别人想不到的采访对象;在新闻热点报道中,发现与众不同的报道视角;在新闻热点报道中,使用别人没有用过的语言报道新闻事件;在新闻采访中,有责任心、有思想,其思想性体现在新闻价值的判断、采访问题的设计、新闻事实的选取。
把新闻学课堂搬到长征路上,是让清华新闻学院的学生在新闻实践中感受新闻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新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他们必须学会在不确定、不稳定和冲突的情况下,运用新闻学基本原理,获取事实真相。让学生们在每次采访中,都有新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在这短短的10天野外采访中,他们实地体验了全世界各地记者都经历的许多共同的问题:新闻故事的寻找、采集素材的新闻评价、采访信源可靠性判断、受众兴趣判断、新闻故事的写作、新闻故事的编辑、新闻语言的运用。例如,对写作语言的要求十分严格,同学们要多多使用街头街角老百姓的语言。故事传达的可能是某种哲学或科学理念或理论,但在新闻报道中不可使用这些学术性语言。
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努力用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判断力,帮助学生发现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需要强调的新闻点、故事亮点和卖点。我尽量不强加自己的观点和叙述框架,为了反映同学们的实际水平,我对他们的语言文字也不做过多的修改。
[i] Theodore Glasser, The Motives for Studying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4, 2001, P.623-627
[ii] Theodore Glasser, The Motives for Studying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4, 2001, P.623-627
[iii] Candlin, E.F, Teach Yourself Journalism. London, 1970 Teach
Yourself Books, P.12
[iv] Burns, L.S, Understanding Jour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5
[v] C. Christians, K. Rotzoll and M. Facklerl, Media Ethics: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 Longman, New York, 1987, P. 147 (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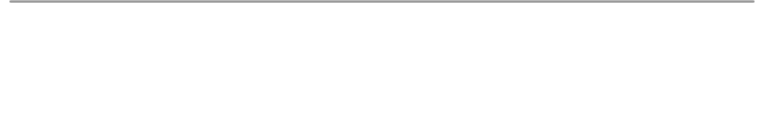 |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们与漂亮的藏族姑娘、英俊的藏族小伙儿手拉着手,围着熊熊的篝火,踢踢踏踏有节奏地跳着欢快的锅庄舞,他们已经是满头大汗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们与漂亮的藏族姑娘、英俊的藏族小伙儿手拉着手,围着熊熊的篝火,踢踢踏踏有节奏地跳着欢快的锅庄舞,他们已经是满头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