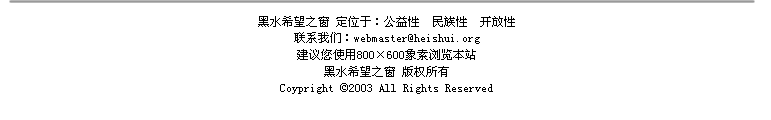|
|
|
|
|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20卷 第6期 1999年11月 雪域风情 民族魂魄 ——蒋永志创作论 杨兴慧 邓经武 内容提要:藏族作家蒋永志在诗歌、散文、小说和电视文化散文创作等方面都进行过辛勤努力,写出了藏民族生存环境的自然形态、地域风情,更展现出藏民族特有的勤劳、勇敢、顽强的人文精神。这既得力于他对本民族人生的深切体味,也有着他在藏族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涵蕴。文章通过对这一个例的分析,思考了文学创作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藏民族 文化 文学创作 学术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I206(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6—0036—05 一 面对一大堆刊物书籍著有“蒋永志”的文字,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诗人、小说家、散文作者、藏文化研究学者,或者换一个角度去认识他:藏族人、知青、林业工人、教师、编辑、作家——我们似乎很难为他给出较准确的定位,我们还是去回溯一下他的人生轨迹。 蒋永志属于在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一代,1946年10月出生在中国西部阿坝州藏羌聚居的青川县,四岁时迎来了新中国的红旗飘扬,在家乡读完小学和初中,又于1966年高中毕业于马尔康中学,但是,文革的发动“粉碎了顺利考入大学的希望之梦”。他和同龄人一样把青春奉献给了那虚幻的政治革命理想。1969年他回到家乡成为“知青”,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知青”这个汉语专有名词,积淀着蒋永志们几多感叹,几多辛酸,又包含着其一代人多少痛苦和愤激?相对于他的同龄人,蒋永志似乎还是幸运的,“接受再教育”时间不长,他就成为一个林业工人。而在当时,众多的同龄人还在“今夜有暴风雪”的严酷生存环境中艰难搏击着,一些人在痛苦绝望和感受被愚弄被遗弃的愤激中,转向偷鸡摸狗游戏人生,而被乡民斥咒为“孽障”时,成为“国家正式工人”曾使多少人羡慕和嫉妒?但已接受充分文化教育熏陶且不甘平庸的蒋永志,体会到的却是“远比农村更为艰苦和寂寞的林区生活磨练”。也许正是这种“更为艰苦”和远离社会“寂寞”的人生体味,使他开始以写诗来充实自己,也许更因为这种“磨炼”使他人生追求的意志更为坚定。 “时代不幸诗家幸”,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拯救了他。艰辛的人生可以把人磨炼得平庸无聊,也可以催人奋起,蒋永志这一代人不乏更具有聪明才华者,但很多却湮灭无闻,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其是否有人生追求。也许是因为他的知识积累,也许是因为他的才干和文笔,他被调去教中学英语和语文,后来又被提拔作宣传干事。这对他的自我提高和知识积累,对他的文笔训练,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与他同龄人中少数佼佼者所走的路类似,1979年他幸运的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应该是他人生转折的一个关键期。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理论的掌握,古今中外浩瀚的文学精品和中外文化丰富宝藏的熏染,使他的思维眼界都跃升到更高境界,也使他对文学的追求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自觉。世界发展趋势的视角,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思维,文化热潮的激荡,都使他开始较为清醒地观照社会人生和审视自己所属的藏文化。 1983年他被调到文学刊物作编辑,个人兴趣爱好与工作方式的结合,业余与职业的统一,蒋永志从此被定格于文学事业。他自谓:“自幼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二是写作。读书从无选,无论文学、宗教、哲学,也无论古今中外,更不分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凡读得懂或似懂非懂的书都读,因此,写作时便凭兴趣”(《个人简历》)。一个藏族“知青”,成长为作家、学者的历程,是值得我们作个例研究的。 二 蒋永志称:“1972年开始了文学创作,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创作题材主要以林区生活为主。”正如大多数作家一样,他是从诗歌写作开始其创作历程的,《高原抒情诗》中收录的40多首诗,就是他初涉文学创作的轨迹体现。 诗集共分三部分,其中“迷人的南方”是作者80年代参加四川少数民族作家讲习班,到中国西南、华南地区参观考察的记录。带着高原雪山的情怀,他吟唱着:“我从雪山来/我从草地来/洱海边,捧一掬醉人的海水/洗濯一路旅程,一路艰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大自然如画的美丽多姿,个人在文学创作上正式起步的踌躇满志,使他看到的一切都充满了喜悦:“洱海两岸,已被深秋染得那么浓/怀里抱着一个沉甸甸的收成/雾消散了,那片片归来的帆正托着一个希望的早晨”,《洱海边,我把脚步放得轻轻》这首诗,在绘写眼前风物景色中作者自抒情思,似乎恰好是作者在经历十年的民族苦难和个人磨难之后开始奋起的预示。 在他的眼中,石林是那样地朴实,“任风雨剥蚀,任游人攀援/高昂着沉思的头颅/但,没有愁苦,也没有哀怨”;海轮甲板上水手那粗犷的身姿,“粗黑的皮肤/是赤道的风和阳光的颜色/斑斑点点的盐渍/是深海给他的吻的印记”,藏族人文性格那剽悍勇武的潜意识就被眼前的人生图景所激活,他渴望着也能在海浪里去“滚一身海腥味/然后有一次用水龙头/从头浇下来的享受”;《海滩上的遐想》表现了作者的人生信念:“纵使死去/也不愿梦幻般漂浮/要找一块坚实的墓地”;也许就是藏族民族性格的潜意识和传统思维格局的作用,他眼中的“西山睡美人”,竟然是:“好一个固执的女孩子/竟然同岁月赌气/要睡,就睡上一万年!”;在滇池龙门,诗人所震惊的是:“啊,你还痛苦地保持着/一瞬间飞腾的雄姿/尾,任碎浪抚弄/头,高昂云天”。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联想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作家的艺术性常常在于看取生活的独特视角,而这种视角又决定于作家思想境界的高低、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决定于作家人生经历所形成的思维格局。作家对人生的审美观照,必须经过感知——认同——选择等几个阶段,也就是说,由于已经形成的心理格局和思维定势,作家对生活的感知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他只看取自己所喜欢并思考着的,同时将自己的情感贯融其中,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感染力就由此而具。 “如花的草原”描写西部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歌颂新时期以来草原人民美好的人生,具有抒情诗的特点。他笔下的草原充满了“绿”:绿的小河,绿的草滩,绿的山丘。在诗里他感叹的是:一个“绿色的梦/在厚重的雪被下压了很久/醒来时已是春天”(《绿》);一条小河九曲十八弯,在作者眼里,它的各种形态都充满着社会内容:“是昔日的辛酸载得太多太多/还是今日的欢乐盛得太满/是冬天的寒流使你卷曲/还是夏天的阳光使你流连?”。在作者的情感浸润下,流淌不息的小河是“到远方讲述草地的昨天和今天”(《小河》)。这些诗作体现着他那一代人在特定时代经历中的感伤情调,表现着时代精神的“伤痕”特征。如果说,草地景物更多的寄寓了作者的“昨天”感伤,那么,草原的人物就体现着作者对新时期美好人生的向往。草地姑娘“豪放的笑声”、纵马奔驰的矫健身姿,还有“蒙住双眼的指缝中/流出醉人的光波一串”的多情(《草地姑娘》),三代骑手的追求和向往以及对草原生活的热爱(《骑手》),赛马场上摩托车“一齐沿着马蹄踏平的跑道冲刺/掀起咄咄逼人的热浪”所体现“高原来不及咀嚼的新思想”(《赛马》),以及《奶粉厂》、《红柳》等作品,都是作者对“文革”以后新生活的热情赞颂。时代的思考与个人感受、新时期的美好与高原民族的生活形态,就被作家具化为“牦牛背上的世界”,把生活、把世界“驮在牦牛背上/惟独把心根植于草原”(《牦牛背上的世界》),这就是作者人生独特感受和站在新时代高度的抒情。 这种感受,以及对作者所属民族的文化寻根,在“高原的雕塑”一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欢笑的高原》、《亚克夏山顶的无名红军墓》等,或追怀“十二个红军兄弟/用年轻的生命使历史凝固/在亚克夏山头的那一瞬间/化作时代的徽记/高悬在祖国的蓝天”,或描写“首届高原艺术节”的热烈欢快,这都体现着作者对自己生存环境的骄傲和政治热情;在历史文化层面,他从牛角号声中感到一种“兴奋和颤栗”、听到西藏古代“赞普时代的召唤”,看到“锈迹斑斑的箭矢/凝固在烟熏火燎的黑色墙壁”,再次体味到“那失去了很久的激动”,藏民族那搏击人生的传统血液在他身上“躁动不已”;“头人官寨”的废墟,使他联想到“早已衰败的是千年赞普之梦”,废墟周围那勃勃繁盛的满山野花绿草,似乎正是“早已成为记忆”的历史见证(《猛河随想》)。伴同高原民族生存的鹰,“生命的经验聚集得太多了/才敢傲视侵入眼界的一切生灵”,面对藏民族人生历史的见证物,作者内心深处体味到的是:“风暴在你的翅尖颤抖/撕片片云彩作投掷的游戏/稳重的山崖也生出骚动的渴念/伸臂相迎作你锚泊的港湾”(《鹰》)。而《牦牛》、《风铃》、《高原的风》、《古道河》等,都是通过青藏高原特有的物体意象,去表现西藏社会人生的具体内容。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写出了藏民族生存环境的自然形态、地域风情,更展现出藏民族特有的勤劳、勇敢、顽强的人文精神。在作者的情感和人生价值观浸润下,青藏高原那严酷的自然,无论是寒冷的冰雪、暴戾的狂风、险峻的高山,还是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骏马,都是孕育藏民族人文性格的物资文化基础。即使是冰天雪地、万物凋零的冬季,作者看到的却是“选择冬季需要勇气/选择冬季就是选择一种超越”;在作者强悍的生存意志的灌注下,严酷的冬季却是一个“石头开花的季节/洁白的冰凌花/肆无忌惮地怒放得漫山遍野”。因此,“选择冬季就是选择一种幸福/大地坚实,蓝天明澈/冬季能使高原凝固/却无法冻结一个民族炽热如火的血液”,“应该感谢高原的风/没有它的狂暴/就没有粗犷的高原/没有它的锋利/就没有一个民族的伟岸”,作者心灵深处不禁涌荡着这样的骄傲:“啊,大概是暴风雨诞生的/生来就需要这样的摇蓝/不然,心中定有一个不变的概念/相信暴风雨,不会/把高原扭曲一星半点/于是,儿子也甜甜地熟睡/在大地伸出的臂弯里/头枕着长长的地平线”。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东方民族文化“天人一体”哲学的精义、藏民族的生存形态和文化性格形成原因,就在作者营造的艺术具像中被生动的展现出来。 如果说,作者步入诗坛之初的林区题材作品体现着70年代特有的政治浮躁和浅薄,我们不难从这样的句子中看到:“歌飞青山山作台/绿色宝库任我开/歌飞大江江面阔/浪花为我送木排”,那么,继《高原抒情诗》之后的一些诗作,就更多地表现着作者在藏民族文化意识上的理性自觉。《茶马古道》组诗四首对古代松州历史的回忆和对藏民族历史的思考,《高原雕塑》二首对青藏高原自然形态所蕴涵文化意蕴的审美观照等,都是这种新特征的代表。 蒋永志在评论文章《勇敢的追求》中谈到:“我们一些初学写作的少数民族作者,甚至也还有不少有名气的少数民族作者,写自己民族时,着眼点往往放在对奇异风情的描绘和神秘故事的编织上,忽略了对本民族历史的、心理的深刻理解和挖掘,因此,许多作品神奇有余而欠深厚,很难使读者激动和思索。”可以说,正是这种创作的理性自觉,是他的作品表现出较浓的文化意识并呈现出特有的文化品位。 三 相对于诗歌创作而言,蒋永志在小说方面的创作数量要少一些,但仍然体现出一定的特色。“深山老林系列”短篇就是描写高原世态风情的现实之作,《生荒》从60年代中国经济极度贫困的背景中,描写了一个中年林业工人邓木良在艰辛的生活中那善良、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的性格,他从对牧羊女五姑的关怀进而发展到爱恋,五姑却由于服从原有“娃娃亲”婚约和遵守当地“不嫁外族人”的习俗,不得已嫁给了愿意作上门女婿的丑陋汉子。失去生活希望的他在恍惚中落水而死。由于小说穿插了开荒度饥与“割尾巴办公室”的矛盾、“三年自然灾害”给藏族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传统道德习俗与人生追求的冲突,这就使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悲剧意义。《远离神山》描写了少年雍中随舅舅去挖药材贝母,冒险去卡西洛神山,巨大收获的喜悦却被一次暴雨雷击所泯灭,出于对神山的畏惧,舅舅要把药材还给神山,雍中则偷偷地把药材带下山换钱供养奶奶。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却表现着80年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意识、宗教意识的冲击,“城里作干部”的父亲另有新欢、母亲愤而抛弃家人等内容,都表现着特有的时代特征。 描写“一个藏族头人的传奇生涯”的记实性长篇小说《归宿》,叙述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四川西部藏区头人的故事。多吉巴让(苏永和)从一个少年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部落征战,在猛河流域建立起一个威震遐迩的“独立王国”,被呼为“猛河王”。后来他又受蒋介石政权指使,用武力抗击解放军并遭惨败,不得已而参加人民政权,却又在50年代中期逃亡国外,并去台湾接受蒋介石的召见和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军副司令兼一纵队司令”、成为达赖集团的“难民委员会代表”、“反共藏汉联盟副主席”。人民中国建设成就的现实和怀乡之情,又使他力图与反共政治拉开距离,他先后流浪于锡金、印度,定居加拿大,在饱尝了背离祖国、远离家乡之苦后,于80年代初毅然回到国内,最后长眠于故乡。 小说着眼于主人公人生经历和政治生涯,按照主人公人生历程的线索,用“流血的部落”、“少年头人”、“猛河王”、“难圆的梦”、“难悔的棋”、“西去‘极乐世界’”、“恒河的迷惘”、“最后的归宿”等章节,全面展现着一个藏族头人那“毁誉参半”的复杂性格特点。同时,围绕着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小说又穿插了大量了藏族民俗风情,如部落之间的交战和世代仇杀、藏区政权的特点和交接方式、国家政权利益与藏部落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婚丧嫁娶和宗教信仰等。这些内容,既真实的展示出主人公性格形成变化的原因,又表现出一段特定社会历史的独特状况,更展现出藏民族特有的人生形态,从而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在细节处理、心理描写等方面,小说也精心营造,文笔优美,可读性强。但是,由于小说取材真实的人物而受到一定制约,又因为小说本为15万字长篇的节略,因此有些细节的连接和情节的展开就让人略感不足,如“西去‘极乐世界’”一章。 散文因其短小精悍和擅长情思表现而成为作家们最喜欢运用的一种文艺体裁,蒋永志在散文领域进行着精心耕耘。1992年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二等奖的《高原有条梭磨河》即是其代表。“梭磨”在藏语中意为梳子,它既是四川藏区的一个地名,同时又是一个女土司的官寨名字,还是大渡河上游流经嘉绒藏族腹心地带的一条河流的称谓,作者选取这样的题材,是基于对嘉绒藏族这样的“接近汉族地区的山谷”人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积淀,表现自然生命与自身生命浑然一体的自然崇拜文化心理。《梨花赋》是基于当地特有的“白色崇拜”文化信仰去赞美梨花“经历过多少磨难,年年岁岁,给人洁白的素花,甜美的果实”,在作者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标准下,“梅花有艳丽的色彩,有浓郁的香味;梨花没有,然而梨花白净得象雪,蜜蜂围着它嗡嗡地转,使人感到生机勃勃。梅花在冰天雪地中怒放,傲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枯枝败草;梨花没有那样的孤傲效果,然而,它却像无暇的白玉,哪怕零落污泥中,也决不改变颜色。况且,看见了梨花,人们的心中就会涌起金秋时节梨子的甜味,这难道不更值得爱吗?”当地“雪梨”遐迩闻名,梨花盛开时“如雪似玉般铺满山山洼洼,晨风吹过, 片片花瓣随风落下,象纷纷扬扬的雪花”等美丽风景,就在作家饱含情感的审美观照中被表现得鲜明生动。《在冰雪的原野上》中绘写的“小屋”、“雪”、“养路工”、“星座”等艺术意象,都体现着浓郁的“白色崇拜”特征。《大渡河的浪花》选取藏民族生活中特有的内容如牛皮船、石栈道尤其是“石头崇拜”价值观下的鹅卵石等客观物质,去抒发人生和文化思考。可以说,这些散文都体现着作者那严肃的人生态度和思考深度。 四 一个作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艺术世界,关键在于找准自我,自我的生活积累以及基于其上的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同时文学创作是一种文化创造,它要求作家对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尽可能地概括把握、理性自觉。也就是说,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意识自觉,对自己民族文化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系统掌握,还有对特定社会人生形态的烂熟于心、深切体味,这些都是养成一个大作家的必要前提。作为一个藏族学者,蒋永志在藏族文化、历史、民俗、宗教等方面研究是极具成就的。1990年出版的《阿坝州藏传佛教史略》、1992年出版的《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以及《嘉绒民俗考》等论著,作为主笔的蒋永志的理论修养和眼界,都得到了较直接的表现。而其学术专著《雪域文化与新世纪》用20多万字的篇幅,从历史轨迹、文化发展与其他文化的撞击、地理和考古、民族传统与外部世界的交汇尤其是化合与排斥的矛盾冲突等多侧面,系统地论述了“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独特文化的产生发展历史和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交汇应该注意的问题。 作者从“这一片被重重大山和茫茫冰雪围困下的高原,却最终形成了具有与世界上任何一方地域和任何一个民族所不同的文化意识、道德传统和价值取向”,他要把被严酷自然环境所封闭、“被历史过于厚重的面纱掩藏得如此深邃与神秘”、向来被认为世界东方文化中最具神秘色彩的藏族文化展示给世界。他对藏民族的起源几种说法进行了辨析,对藏文化几种特征给予具体的阐述,将之概略为地域性、宗教性、整合性,又从其2000多年一贯的历史脉络,去审视其曾有的辉煌与滞后的各种原因。其中又辅以历史、地理、文化、哲学、考古和人类学等理论方法,这都使该书呈现着浓郁的学术理论色彩和研究参考价值。可以说,作为一个藏民学者,蒋永志的藏族文化研究成果,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多民族文化整合、建设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是有价值的。而对他自己来说,这种学术研究对他的创作思维、审美价值判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个作家必须把握其所处时代的审美思潮,必须应和社会的审美期待,20世纪新兴的艺术种类、被人们视为本世纪时代艺术霸主的是影视艺术。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种新兴的艺术提供着物质基础,声像并茂的直观性为尽可能大范围的普通大众接受欣赏提供着可能,尤其是在社会飞跃发展、一切都是快节奏的今天,人们无暇从事宏篇巨制的阅读,影视艺术自然地成为最受社会大众欢迎的艺术种类。可以说,当今活跃于文坛的许多作家都以投入影视艺术领域为荣,是为“触电”。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可以去把握蒋永志在电视文化艺术片剧本方面创作的意义。 作者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首先是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去切入影视艺术。作为一个在藏民族地区生活多年,对本民族人的生活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民俗民情烂熟于心的学者,他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他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都决定着他看取人生、选择题材的特有方式。这首先体现在他出版的旅游散文集《九寨黄龙草原》中,而《走进川西北》、《阿坝风情录》、《梵乐声声》等电视文化艺术散文的创作,更集中地表现着他的文化修养和文字表达功力。 《走进川西北》是作者对自己所生活土地的热爱与自豪的表现,他这样饱含激情的写到:“当我们走进这片土地,看见的不仅仅是童话世界般的九寨沟,梦幻般的黄龙风景,九曲黄河流淌过的大草原,看见的也不仅仅是遍地林立的经幡,古老的石碉、寨楼。在这里,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历史艰难延续的过程,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文化层次积淀的景观,是深深浸润着中华5000年文明的神奇土地。深处的驮铃,仿佛从遥远的历史从走来,让我们追随那千年的蹄印,走进川西北,走进阿坝州,走进高原辉煌的昨天。”在《茶马之路》一集中,作者形象地展示出高原特有的自然景观:“一只孤独的鹰在蓝天游弋/草原尽头的雪山静穆的耸峙着/无数的雪峰在云海中浮沉”,又从历史的角度对茶马互市的形成、藏民族与内地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各自政权的更迭等方面给予具体解说,从而体现着厚重的历史感。《石碉奇观》、《藏寨奇趣》从藏民族生活的物质积淀中、《遍地神灵》、《浪漫婚礼》等从民俗风情的角度,全面地表现出这块土地的神奇可爱,从而体现出浓郁的文化色彩。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上海东方电视台才将之投拍,并且放映之后立即受到社会的欢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蒋永志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的辛勤努力对其作品特征形成的作用,他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作家必须立足于自己民族之根,必须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去发掘生活的意蕴,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文化、历史和哲学的眼光去思考,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鸣谢文字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20卷 第6期 1999年11月)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