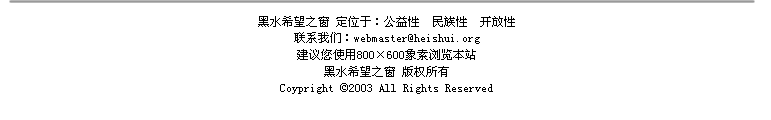|
|
|
|
|
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 李绍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识别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956年8月,费孝通与林耀华两位先生于《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将“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列为当时民族学研究四项任务的首项(其它三项任务分别为“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及“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反映出当时的这一实际。1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中央民委派调查组进行畲民识别以来,迄至1987年2月10日国家民委以“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答《民族团结》记者问为止,其间经过30多年时间。这段时间,经国务院确定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成分,除汉族外的少数民族有55个之多,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即民族成分的问题,其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在某些地区还存在人数不多的少数族体的民族识别问题。这些遗留问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研究,并逐步加以解决。 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多少民族?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是含混不清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而实际上我国的民族又何止汉、满、蒙古、回、藏五族。这是由于在当时,尚不具备彻底弄清我国民族构成的客观条件。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期,沿海沦陷,大批民族学者相继迁徙到内地,尤其是在西北、西南等地,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并取得一定成绩,但离彻底弄清我国民族的构成情况仍有相当距离。新中国的建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但这事先必须弄清我国的民族构成方能入手。在195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族别称谓即有400多个,因此民族识别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民族识别的初步调查研究,要求能基本上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2 195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族别称谓达400多个,情况相当复杂,此后经过分析研究,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1.有的称谓系泛称,比如历史上称中原以外四周各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到50年代初,这种泛称仍然存在。如贵州将少数民族均称为“苗”,其中又有“仲家苗”(布依)、“侗家苗”(侗族)、“水家苗”(水族)等等,并不限于现今的苗族。 2.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自称。如彝族中多数自称为“聂苏”或“诺苏”以外,还有“阿西”、“撒尼”、“子君”、“罗武”、“密岔”、“山苏”和“车苏”等等支系的自称。 3.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居住地不同或方言区不同的自称。如傣族因住地不同有“傣”、“傣纳”、“傣崩”和“傣雅”等自称。纳西族因方言不同有“纳西”、“纳恒”和“纳日”等自称。藏族中因住地与方言不同有“博巴”、“康巴”、“安多哇”和“嘉绒”等自称。 4.有的称谓系因服饰或生活习惯不同的他称。如苗族中有“青苗”、“白苗”、“花苗”和“牛角苗”等等。仡佬族中有“花仡佬”与“披袍仡佬”等等。傣族中有“旱傣”、“水傣”和“花腰傣”等等。 5.有的称谓系因信仰同一宗教而来的他称。如伊斯兰教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称回教。因此,有的便称讲汉语的回族为“回回”,称缠头的维吾尔族为“缠回”,称东乡族为“东乡回”,称保安族、撒拉族为“保安回”、“撒拉回”等等。 6.有的称谓系不同民族自报的相似名称。如湘、鄂、川、黔有土家族,青海有土族,而彝族中也有自报为土族或土家族的,皆含有土著的意义,实则并非一个民族。 7.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沿用了历史上不同称谓而来。如白族中有的自称“白子”,有的自称“人”,而有的则自称“七姓民”等。 8.有的称谓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汉民集团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形成的自称。如贵州的“南京人”、“湖广人”和“穿青人”;湖南的“佤乡人”和广西的“六甲人”等等均是。 有如上述,可见各民族族称的情况相当复杂,从而为民族识别带来了艰巨的任务。根据上述实际,我国民族学家们用马列主义民族学理论为指导,对国内各民族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从1953年起至1957年,明确了11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后又相继明确了9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中基诺族是1979年才得以确认的。 关于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已有黄光学、施联朱等同志所编《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进行了总结。3该书将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大体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端阶段(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这一阶段对畲族、达斡尔族进行了调查和确认,将新疆的“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将新疆的“塔兰其族”归并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经过识别和归并,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从自报的400多种民族名称中确认了39个民族成分。 第二阶段——高潮阶段(1954年至1964年)。这一阶段对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地自报不同称谓的民族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并将74种不同称谓的少数民族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当中。 第三阶级——受干扰阶段(1965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除确认西藏的珞巴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以及在贵州进行了一些民族识别的调研工作外,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民族识别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第四阶段——恢复阶段(1978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除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是恢复、更改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自1982年以来,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500万人,这段时期已恢复和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辽宁和河北的满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几省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侗族、苗族和四川东部的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止,我国已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至此,全国的民族构成基本弄清,民族识别的基本任务业已完成。 二 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工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的,其中有不少新的发明与创造。 民与族二字在我国早已使用,但所指的为某一具体的族体,而无抽象的概念。直到近代才有将“民族”二字合并使用的情况,但“民族”与“种族”两词经常并称混用,而无科学界定。时至今日,西方的学术界仍有将民族(Ethnic)与种族(Races)混用并称的情况。实则种族是一个血缘的概念,而民族虽然含有血缘的因素,但主要是一地缘的概念,二者的内涵是不同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发展观,将民族共同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原始社会;部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按照这一理念曾将境内的一些先进的族体划为社会主义民族,另一些后进的族体划为社会主义部族。在我国民族识别中,如何全面地理解和正确地运用这一理念,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中大多数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段,而有的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或农奴制,甚至有的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浓厚残余。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民族识别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虽然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不平衡性亦将会长期存在,但新中国建立后的各族都已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若仍将一部分族体称为民族,而将另一些族体称为部族或氏族、部落,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在政治上有违民族平等的精神也是不可取的。因之,确定将新中国境内的各族都一律统称之为民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的正确性。 我国民族识别所依据的民族概念是斯大林为民族所下的定义。斯大林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4斯大林这一关于民族的论述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阐明了民族的实质,是迄今最为科学的民族定义,必须作为我国民族识别时的思想指导,但在结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时,又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全面、系统地理解。应该看到,斯大林所概括的这一民族特征是从欧洲各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民族出发的,因而它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而言就应更有灵活性。这也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在我国民族识别中,既要重视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四个特征同时存在的必要性,又要注意到这四个特征具体存在于某一民族时其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 首先是共同地域。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都形成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同时,又与其他民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比如回族有860余万(1990年),而聚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仅152万人,其余的则分别散居于全国各地。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回族,既有较为集中于回族自治州、县的,也有完全散居于城市与农村中的情况。又如苗族有739万,分布于贵州、湖南、广西、云南、湖北、四川等省区200多个县内,没有连片的共同地域,但在某一省区中却又相对集中于苗族自治州、县。又如瑶族有213万,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和江西等六省区,亦无大片相连的地域,长期处于“大分散,小集中”的状态,人口最多的地方建立了自治县。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要看到民族必须具备共同地域的这一特征,却又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必须要具有完整的连片的共同地域的认识。 其次是共同语言。我国的少数民族中,目前回、满、畲等民族基本使用汉语。还有同一民族讲几种语言的状况。如景颇族中景颇支讲景颇语,载瓦、茶山、浪速三支讲载瓦语。又如裕固族,居东部的讲恩格尔语,居西部的讲尧呼尔语,二者语系不同,不能交际。再如瑶族,一支自称“勉”的(占整个瑶族的70%)讲瑶语,一支自称“布努”的讲苗语,一支自称“拉加”的讲侗语,一支自称“丙多优”的已讲汉语。再如藏族,多数人讲藏语中的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但还有十几个小群体讲藏缅语族中的另一些语言:“嘉绒”讲嘉绒语,“白马”讲白马语,“木雅”讲木雅语,“贵琼”讲贵琼语,尔苏讲尔苏语等等。据研究这些语言属于羌语支中的语言。即便讲同一语言的民族,由于以往交通不便,很少往来,形成了许多方言、土语,彼此也很难沟通。这在苗族、彝族等民族中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共同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也要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作具体分析研究。 第三是共同经济生活。一个居住较为集中的民族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自不待言,但居住较为分散的民族则很难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存在。比如有650万余人口的彝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区,民主改革前分别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和奴隶制经济等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其中大小凉山的彝族有120余万,其奴隶制经济一直保留到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整体的彝族,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如此之大,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经济生活。这是问题的一面,但却不能就此否认相对聚居的彝族,在一定范围内也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比如四川凉山州内的彝族原来主要是奴隶制经济,云南红河州内的彝族原来还保有封建领主制经济,而云南楚雄州内的彝族原来则主要是封建地主经济。此外,在历史上还有不少汉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且多居于城镇,其社会经济必然辐射到四周的少数民族。在研究少数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时也不能完全 第四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是指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乃至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一点在我国的民族识别中较少引起歧义,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起到了唤起民族认同的作用。共同心理素质,归根结蒂可表现为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感。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关键在于民族意识。比如散居在我国各地大量的回族与满族群众,其聚居地域、独特语言与特有的经济生活已不复单独存在,但他们都仍保留着自己固有的共同文化与民族意识。因此,民族意识并非不可捉摸可有可无的东西,换言之它往往是民族识别中考虑是否为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 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除了上述民族的四个特征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外,根据实际情况还须着重考虑下述两个原则。 其一,注重各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渊源。各民族的自称与他称均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它的来龙去脉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认定,因此必须认真考察清楚。各民族都有其来源与分流,在我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与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各民族口碑相传的民间传说中,反映出他们的历史渊源。这对于民族识别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素。 其二,注重各民族的意愿。民族意愿是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的具体体现,在民族识别中必须加以尊重。民族识别工作中提出的“名从主人”的这一原则便是据此出发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应该与各民族所具备的特征相一致,这是民族识别科学性的体现。但是,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一些民族的成员缺乏对本民族全面、系统地了解,在民族识别中有时会出现某一部分人的民族意愿与本民族民族特征不相一致的情况。这样,作为民族识别工作者则有义务协助该民族的成员来作好解释与协调工作。当暂时不能说服该民族或其中某一部分成员时,一般采取暂缓作出硬性决定,或者采取“名从主人”的办法,以暂时维持原状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在我国民族识别的实践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几乎都没有完整地具备着作为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因此,绝不能机械地用是否完整地具备四个特征的看法套用在我国尚未充分发达的各民族的头上。但是,又要看到我国的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业已基本具备了这四个特征的刍形,只是这些特征表现出不平衡性,有的民族这一特征较为突出,而有的民族另一特征较为突出而已。这就要求我们综合地、全面地来衡量各民族的特征,而绝非教条式的生搬硬套。除此,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还根据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应该注意各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渊源和注重各民族意愿的原则。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于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我国民族学科一笔丰富的理论财富。 三 我国民族识别取得的巨大成就,世所瞩目,其经验对于第三世界的多民族国家解决类似的问题,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目前,我国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虽然已基本完成,但尚未彻底结束,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进行,其前景相当可观。兹略述个人管见。 首先,要继续研究民族识别的理论问题。从宏观上来看,民族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有其发生、发展、变化乃至消亡的过程。自从民族形成以后,民族共同体一直处于分化或融合的过程中。在历史上的民族有的得以发展至今,有的则分化成许多新的族体,有的又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或与其他民族组合成了另外的族体。因之,民族的演变过程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既然民族共同体在不断演变之中,则民族识别的研究也是我国民族学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继续总结以往民族识别的经验,研究民族识别的理论,密切注意民族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发生的新问题。 其次,要解决民族识别中的遗留问题。前已言及,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尚有一些遗留问题未曾解决,1982年以来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500万人,其中已恢复和更改了260万,尚余200余万。此中固然有的不属于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之列,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有待今后解决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第三,要解决在民族识别中因种种原因形成的一些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展的时间并不一致,有时还是分省区进行,这就造成省区之间对同一民族有不同认定的情况。比如云南的普米人在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单一民族,而四川境内的普米人则划入了藏族当中。又如四川、云南毗邻的泸沽湖畔的纳日人(摩梭人),云南民族识别时,已归并到纳西族中,成为纳西族的一个支系,而在四川的部分却成了蒙古族。此外,也还有因其他原因造成名不符实的情况。比如四川西北部黑水县的主要居民为羌族,因长期受藏族大头人多吉巴桑(苏永和)的统治,建国初期,将他们报为藏族,迄今这部分人仍称为“讲尔玛(羌族的自称)语的藏人。”凡此种种,均应在今后根据该民族的意愿经过充分协商逐步予以解决。 第四,要对港、澳、台的民族识别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祖国,成为中国的一个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澳门亦将于1999年回归祖国,成为另一个特别行政区。根据我国既定方针,中央政府不干涉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但港、澳从未进行过民族识别或类似的研究,因之对该地的民族构成迄今仍不清楚。鉴于对国情和特别行政区区情应有明确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民族构成的认识,中央应组织力量对港、澳的民族识别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港、澳的回归必然对台湾产生重大的影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省必将统一于中国。关于台湾的少数民族,我国一直沿袭以往的称谓,统称之为高山族。根据近来台湾民族学界的研究,已认定高山族中有9个民族,即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雅美和赛夏等民族。而台湾的少数民族中原来还有平埔族的说法。平埔族也是一个统称,据研究其中可划分为10个民族,目前除邵族的一部分还保留原来的部分语言与习俗外,大多数已在历史上与汉族融合。如此,现台湾当局已承认的少数民族有10个之多,1997年1月笔者访问台湾时在宜兰县得知该县已承认了居于该县一带的噶玛兰人为单一的民族。51996年12月,台湾的“行政院”建立了“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拟逐步理清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称与结构。为适应这一形势,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于1997年初开设了“民族认定”的讲座,笔者亦应邀进行了中国大陆民族识别问题的系列讲授,他们意在借鉴大陆民族识别的经验以加强对台湾民族识别的研究。大陆素有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与经验,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亦可进一步探讨海峡两岸民族学界进行合作研究的可行性。 注 释: 1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23页。 2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3《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4《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5关于噶玛兰人的情况,可参见杨宪宏编:《宜兰:台湾人心灵故乡》一书的《原住民》一章,台湾花王公司1996年1月第3版,第78—80页。作者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邮编:610011) Abstract:InordertocarryoutState’spolicytowardsnationalities,Nationalityidentificationwasaveryimportantwrok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NewChina.B (来源:《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
|
|
|
|